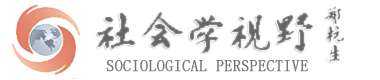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 (下)
孙飞宇
原文刊于:《社会》2017年第2期
[摘要]在上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本篇试图集中到弗洛伊德的五个经典案例,通过约翰·奥尼尔对于这五个案例的理论思考🤷🏽♀️,将精神分析传统中的忏悔现象及其理论置于经典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并最终将讨论落实在生活世界中的理性与存在问题之上✌🏻。文章最终回到黑格尔,主张理性必须落在此在之在(Da-sein)并因而是个体存在之意义世界中。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form of being)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will of life)的理性。第二种理性,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可能是理性真正的困难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
[关键词]忏悔者 生活世界
弗洛伊德一共发表过五篇长幅的案例史。这五个案例史的主角分别是小汉斯🛀、多拉、狼人2️⃣、鼠人和薛伯。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他们的年龄分别为5岁、18岁、23岁、29岁和61岁🏢。弗洛伊德发表这五个案例的时间分别为1909年、1905年、1918年👨🏽👈🏻、1919年和1911年,写作时间各自还要再向前一年至数年不等✶。发表时间的顺序与五位主角的年龄长幼并不对应。不过,这一点并不会妨碍尊龙凯时娱乐按照年龄顺序在整体上理解这五位主角🕴🏼。五位主角的年龄序列,正好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序列,亦即成长的过程。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遗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去图像,获得理念🍪,同时患病👰🏿♂️,并在忏悔中寻求自我治愈。这一在忏悔中治愈的过程,亦即回溯的过程🏪,就是一种回忆/回归的过程🤾。回忆/回归是以形象 (image) 的方式发生的。重返童年🌲,正是梦的机制。
然而重返并非真正的重返。忏悔者对于自己首先要有一种客观化的感知,即一种作为他者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就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反映,正如病态之于正态。自我之于自我的客体感👨💼,是一种将自己排斥出自己的结果。这种排斥的状态,必须要用一种将其排斥、产生排斥的语言才可能描述。所以,这就必然产生一种悖论:忏悔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语言遭遇到了它的背面。弗洛伊德将梦🔆、症状等全都纳入了语言的范畴🈸,以便实现这一忏悔。然而这还不够👩🏿💼,他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文体,一种独立思考的、活生生的写作方式。后来者如果想要真正阅读弗洛伊德🩲,就无法不经由这一点而进入其文本中🧑🧑🧒,并在其中丢失自我或者找到自我。
这也是尊龙凯时娱乐之所以要在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交互之中来讨论忏悔问题的原因。保罗·利科在其早期作品《恶的象征主义》一书中,首先批评了这样一种研究忏悔现象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临时采用了这种信仰之灵魂的动机与意图。他并不会用他们最直接的质朴去‘感觉’他们,而是用一种中立化的态度,在一种‘正如’(as if) 的态度中去‘再感觉’。但是这种现象学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思……”(Ricoeur, 1967: 19)🧙♀️。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要尝试一种移情式的写作,尽管这一尝试仍然要从铺陈开始。
一🧑🏽🏫、 忏悔者与生活世界
福柯在其著作中曾检讨过西方历史中古典时代的忏悔现象,然而众所周知,他并没有详细讨论过奥古斯汀、卢梭和弗洛伊德。1奥古斯汀的忏悔被认为开启了西方文明传统中关于内在自我的思考维度——尽管这一自我与现代人的自我并不相同 (Cary, 2000)。此外,与现代的忏悔主体不同,奥古斯汀真正感兴趣的并非经由忏悔了解欲望,并通过欲望来发掘人的属性🪔,而是“为了知道他是否有罪”,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真理并不在于这个内在的自我”(Taylor, 2009: 30)🛄。
1. 福柯未曾详细讨论精神分析的这个事实甚至成为学界对于福柯的批评之一 (Towes, 1994: 133)。
在弗洛伊德之前🕺🏼,现代关于忏悔的意象以卢梭最为清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卢梭《忏悔录》的典型结构在于开辟了一处空间🧑🦯➡️🚆,以供他反思自我,其中的大量文字所渗透着的力比多使得卢梭的工作成为弗洛伊德式忏悔的先驱——卢梭的忏悔产生了一种文体,该文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力比多的渗透。就此而言,这是一种自恋的文体,力比多投射向了自我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卢梭的忏悔中,或在任何一种此后的忏悔中,都存在着一种作为现代之特征的自恋式倒影——自我投射🦎👩🏽。作者/叙述者进入了一种自己的投影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忏悔可以与弗洛伊德的工作放置在同一个传统之中。现象学地看🧘🏿♂️,忏悔是一种对于已经消失 (Fort) 之事件的重现/再造,是一种召回 (da)👨🏼⚕️。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之原则》中所讨论的经典儿童游戏 (Fort/da) 在此成为忏悔的基本形式🔭。弗洛伊德 (Freud, 1984:285) 认为,这一游戏乃是儿童进入文明状态的“伟大的文明/文化 (Kulture) 成就”2🎑,也就是驱力的克制🪐。也即🥍,只有在忏悔结构中,人才有可能进入文明状态。这一结构不仅体现在儿童的小小游戏之中,也是弗洛伊德在《图腾与塔布》一书中讨论良知👩🏼🎓、罪恶等文明道德问题时的基本结构。需要强调的是,在弗洛伊德式的忏悔中👨🏿🌾,忏悔因为其治疗功能而具有的特征之一就是语言重新具备了儿童期的万能论 (omnipotence) 状态🗼☃️。这一状态既是弗洛伊德赋予儿童期的典型特征🪯,也是弗洛伊德式忏悔治疗的典型特征。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重合的原因乃是患者具有重返儿童期的特征。也就是说💆🏼♂️,忏悔在治疗中得以有效的基本依据在于,该治疗依据患者的状态而充分运用了儿童期的属性。
2. 弗洛伊德在《一种幻觉的未来》一书中曾明确表示过,“不屑于区分”文化和文明👨🏿🎤🥫。他所用的德文原文Kulture一词兼有二者之意。
除了卢梭的作品,关于现代社会中忏悔现象的另外一种版本是由福柯提供的。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研究了在基督教时代所发展出来的忏悔方式是如何逐渐通过一系列变迁而进入现代灵魂的欲望与本能 (intuition) 之中的。在整体层面上,由于人口成为现代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核心学科,而“性”又是这一学科的核心预设,所以🔮,在福柯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在关注到关于人口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时,是将每个个体对待性的态度与社会整体的福祉和未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Foucault, 1978:25-26)。根据福柯的研究,这一点不过是延续了此前在宗教时代忏悔的核心关怀而已👳🏻♂️。所以,福柯 (Foucault, 1978:61) 说:“从基督教的忏悔到今天🧎🏻♀️➡️,性都是忏悔的首要主题👩🏻🦯。”
二、 现象学地看
尽管有些困难,尊龙凯时娱乐还是希望能够将舒茨以现象学的方式所做的关于说者与听者的讨论纳入尊龙凯时娱乐的视域。说者与听者的彼此理解建筑在对于对方的建构性理解之上。尽管舒茨的工作建基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之上✶,而弗洛伊德的工作建基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但尊龙凯时娱乐还是试图在前述保罗·利科工作的前提下🧜🏽♀️🤾🏼♀️,运用舒茨的工作来理解弗洛伊德工作中的部分特质🕴🏻🧑🏼🎓,因为说者一旦想起某事或者某物,那么对于说者与听者来说,就立刻进入到了一种多元结构的活动 (polythetische gegliedert Akte) 中:“这个活动包括了持存与前摄✫,掺杂了再造与预先回忆🙎♂️,也衔接了多样的侧显和交错🕡,而两人都可以把这个活动交替地当作单元的整合体 (monothetische Einheit) 来加以看待”(舒茨🛷,2012:160)🍋🟩。听者以当下的立意来听,故而说者无法确定听者对于所听到的内容到底如何判断。对于这一听者亦即诠释者来说,通过当下的语言或者符号追溯说者预先的构想或历史🧑🏻🔬👩🏽🔧,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行动。弗洛伊德的工作固然需要以一整套解释框架来进行治疗和案例写作🪟,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行动的整全性只有在构想的跨度 (Spannweite des Entwurfes) 中才得以形成”(舒茨,2012:147)。也就是说🏄♂️,无论对于弗洛伊德还是对于患者来说,忏悔所带出的整体性故事都需要构想的过程加以实现。两种构想可能相互冲突🦶🏽,也可能相互促进甚至是耦合👨✈️,更会彼此间展开无穷无尽的诠释与再诠释。这有点像彼此相对的两个镜面,然而现象学的视域依然会强调立意,也就是说🥅,两个镜面所反射的重点永远不同🎗。在这重重叠叠的理解✢🧿、误解、沟通💈、再误解的过程中,诞生了弗洛伊德的谈话式治疗与联想法。作为这一疗法的反映🏄,弗洛伊德文本的特征就在于对于这一切的保留👞。在这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著作有了戏剧论的色彩,对它的理解必须考虑到文体角度🤏🏻。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提供了一种关于弗洛伊德的案例发生学研究。奥尼尔充分意识到了在案例写作过程中历史与知识的书写角度以及读者的角度🐻❄️,并由此开始了理解弗洛伊德的努力🥿。
不过,奥尼尔还是在福柯的基础之上展开工作的。在《性经验史》中,福柯 (Foucault, 1978: 61-62) 这样界定忏悔:“一种话语的形式,在其中👩👧,言说的主体也是该陈述的主体;它还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之中打开的仪式,因为人不会在没有旁伴出现 (至少是实质上的出现) 的情况下忏悔;这名旁伴不仅是一名谈话参与者,更是这样一种权威:要求忏悔,规定与领会忏悔,干预忏悔,以便评判、惩罚🦽、宽恕🍒、安慰🧈、和解的权威”。福柯继续在两个方面界定忏悔:首先👩🦼➡️,在这种仪式中,必须要克服障碍与困难,唯有这样,真理才会被生产出来;其次,它会产生纯净化和救赎的效果。在这种界定的背景下,尽管如前所述,弗洛伊德曾表明过其实践中的谈话与忏悔并不相同 (Freud, 1986),然而在尊龙凯时娱乐的研究中,这二者并无不同。
性倒错的出现使得忏悔的合法性和内容都得到了保证,然而,这一概念的出现绝不仅仅意味着权力的简单禁止😨。它从各个方面保证了新的真理生产机制以及人的生产机制💁🏿♀️,同时吻合了现代性科学的观察和研究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福柯 (Foucault, 1978: 41-45) 认为,现代社会本身是性倒错的🧑🏻⚖️。这并不是因为各种“文明进程”式的禁制的出现🕴🏻,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性倒错被纷纷生产出来🥏,成为问题💆🏼,同时也成为理解现代性个体的方式。福柯 (Foucault, 1978:48) 说🩰:“快感与权力并非彼此消除或相对🧚🏽♂️🦁;它们互相追逐🤹🏼、重叠并彼此加强。”所以,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压抑,福柯有了新的理解:现代工业社会并非逐步增加了性压抑。这一假说并不确切。性科学的发展绝不仅仅与研究相关,恰恰相反👩🏽💼👑,它从来都与最广泛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福柯 (Foucault, 1978:54) 说:“观察整个19世纪🧗🏻,性似乎被容纳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秩序中:一种是关于生产繁殖的生物学🤔🖲,该生物学根据一种一般性的科学化规范而发展;另一种是关于性的医药学,其发展所依据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
总之💃🏻,关于性的科学及其词汇都要受到道德、经济和政治及其变迁的影响。福柯 (Foucault, 1978:55) 认为,在19世纪,关于性的科学中还存在着“系统性的盲目:拒绝去看,拒绝去理解;关键在于🦸🏻♂️,甚至是拒绝关心真正的事情本身”。存在着一系列对于真理的遮蔽与忽视🏄🏽♀️,同时大量的话语又围绕着性建立起来。这二者相辅相成。在这里𓀓🦩,重点在于🧑🏼🦳🧝🏿♀️,性本身成为真理征战的场所:“性被建构成了一种有关真理的问题”(Foucault, 1978:56)。“讲出关于性的真相”成为一种运动机制✍🏽,与这一热情相应的就是关于性的科学 (scientia sexualis),而这种科学的实质就是忏悔🌍:“忏悔成为西方一种最具价值的真理生产技术”(Foucault, 1978:59)🧚🏽♀️。
然而,这只是忏悔的表面现象🎈🤙🏿,因为“真理性的忏悔已经被权力铭刻在个体化的进程之核心中了”(Foucault, 1978:59)🫵🏿🙇♀️。在这一意义上🧙🏼,奥尼尔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所切入的角度,同时也是奥尼尔要求尊龙凯时AG研究的应有之义,正是通过弗洛伊德的五个长篇案例史来深刻理解忏悔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现代人之生产的方法论的。奥尼尔将精神分析视为社会理论的工作,也将精神分析理论视为一种爱人的话语。然而社会理论如何去研究爱?这个问题或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提问,正如当今各式各样对于爱情的心理学研究⚃、对于家庭的尊龙凯时AG研究一样,从一开始,或许就错失了其问之所问、被问及之物与问之何所以问。作为一名现象学家的奥尼尔⚾️🤹🏼♀️,所观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灵魂的原初现象学🧫,再进一步运用“灵魂”来作为灵与肉交弥在一起的场域,并在其中将这一关于原初的现象学复原为意识与无意识的行为——这在他对于狼人的原初场景的分析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是贯穿奥尼尔对于弗洛伊德五个案例之研究的线索之一,也是他分析弗洛伊德文本的入手之处。
在其早期论文《现象学可以是批判的吗?》一文中👨🏫,奥尼尔 (O’Neill, 1972) 就已经显露出了某种同时既生成结构又去结构的视域观与表述方法🧑🏿🏫。这一写作手法在他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更是运用得极为成熟🧘🏽♂️。原因在于,奥尼尔在这样一种观看之中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去结构/结构👞🙍🏽♂️:
我视精神分析理论为一种爱人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那些理解和领悟的喜悦时刻🧗♀️。不过,如果想要避免枯萎凋零,这一话语就不得不摆脱这样的时刻👩🦼➡️🧛🏻。所思所想😾,无非都徘徊于经济/秩序和越界之间,踟蹰于优雅自矜和无止无境之间👩🏿。(奥尼尔,2016:3)
借助于某些通路🏅,思想或许可以“将死亡 (Death) 或爱 (Love) 设为自己的目标,作为其灵魂的女士 (Lady)”🧑🏭。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位置,因为“灵魂自身当然也会被它自己的梦境❤️🔥、幻觉和知识所猎取🩴,所困扰……”🙂↕️,也就是那些“从灵魂的无意识亦即它的创造体中生发而出的梦境、幻觉和知识”(奥尼尔📶,2016:3)𓀀。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是奥尼尔发现了精神分析与某种双重诞生之间的亲和力🕵🏻♂️:尊龙凯时娱乐每一个人在母体 (mother-body) 之中的起源以及“给予生命的欲望之起源”。这一欲望既有其生物性与身体性,又有其社会与文化性。简言之🌗,既有母亲一般的性质 (如同母亲生育每一个“尊龙凯时娱乐”),又有父亲一般的特质 (如同父亲生育法律、艺术与科学这三位一体的自体/单性繁殖领域)👇🏿🍭。然而这两种都堪称单性繁殖 (parthenogenesis) 的幻想——奥尼尔相信这一单性繁殖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将弗洛伊德的工作置于欧洲文明史之中的主要研究线索之一。
这一爱的主题与言说相关🙋🏻♂️。精神分析同时也是一种纠缠于上述言说中的言说。精神分析必须要言说。这意味着,不仅卡萨琳娜与多拉需要言说,狼人与鼠人也需要言说🍻,甚至于小汉斯,也需要在父亲的报告之后,亲自登门去见那位家里有着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安娜的教授先生🧸,甚至于薛伯,也必须要在其“忏悔录”之外被弗洛伊德言说。最后,弗洛伊德还要背叛所有那些向他忏悔之人▪️,向世人言说🧼,以便成全精神分析本身,正如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在分析中,忏悔从未开始👘,永不结束🐯。精神分析仅仅处理语言之中的疾病,或者说,语言的缺失。奥尼尔将弗洛伊德对于疾病的处理🗜👰🏽♂️,以及关于这一处理的所有洞见与盲目、成功与失误、控制与溢出,都视为一种存在之绽出。所以他说☸️:
一种疾病的界限,在于其语言的缺失。一次治疗的开始🤘🏼,是某种症状以另一种语言,在身体之上😶、在梦中🤽♀️、在言语中或是在写作之中,对它自己的关注。(奥尼尔,2016:4)
在这一关于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去结构/结构之中,那位家在维也纳山坡路19号的分析师弗洛伊德首先成为了一位听众👩🏿✈️,然而这位听众👱,同时作为尼采意义上的歌队成员,在聆听的同时也在阐释🫵🤡,并“力图重构这样一种家庭🙇🏽♂️:于其中🧑🦳,病人的故事发端,并且作为一种有自身风格的症候学而发展演变。一门小小的艺术,从某种疾病的案例中,抽离出疾病的过程🚴♀️,从病人那里,抽离出诗歌……”(奥尼尔,2016:4)
所有的案例史💺,在这一过程之中,都成为了爱的故事,正如克莱蒙特 (Clément, 1983: 143) 所说:
精神分析师是爱的生物,而精神分析则是一种多情的规训☠️,一种爱欲性的理论✪,一种纯粹享乐的技艺🤟🏿。
然而精神分析的言说不止于此🤧。这一忏悔还包括言语间的沉默黯淡之时指尖的微微挪动与空气中氤氲的烟气,以及在言说绽放过程中的遮蔽🤵🏻♂️🍓。弗洛伊德借助于对时间的改造而把握这一存在状态。他那著名的关于快乐是对于史前愿望的“延迟性满足”(nachträglich) 以及对于官能症的界定,才是奥尼尔做出如下大胆判断的起因:在弗洛伊德之后,尊龙凯时娱乐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阅读必须要经由弗洛伊德本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完成其旅程,“这五篇案例史构成了一种关于家庭与家庭的无意识想象,关于家庭的剥夺、嫉妒、愤怒与谋杀性的伟大的现象学”(奥尼尔,2016:10)。
三、 案例剧场
(一) 开始与神隐
精神分析的案例通常被理解为故事。一切故事都有开始,哪怕这一开始没有开始。开始的通常意象是出生,或者黎明与童年,或者就像故事常说的那样,在很久很久以前……正如许多人类学家和尊龙凯时AG家一样,弗洛伊德坚信关于“开始”的研究会带来对于“当下”之性质的真正深入理解。弗洛伊德不仅坚信这一点,而且还通过其诊所工作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思路当然有其思想史之中的渊源,然而也的确可以说带有现象学还原的气质🟥。在这一开始之中🙇🤦♂️,如前所述,福柯将生殖之性与规训之劳动关联在一起,将它们视为理解现代人之本质的核心线索📢。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的传统中,这二者也确实堪称是理解人之为人的核心议题。不过,生殖之性与劳动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两大议题,不仅仅是卡尔·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核心议题🧕🏼,更是在西方文明之中对于人之为人在最初的基本界定。在《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在将亚当与夏娃驱逐出伊甸园𓀕,令其成为可朽之人的时候😎,对于二者的规定⛹🏽♂️👦🏿,即是夏娃需要承受生殖之苦,而亚当则必须以劳动来求生。权力🅰️、知识与性经验的三位一体,在西方文明之中,并非仅仅是现代的产物,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作为一种可把握的开始💂🏻♀️,弗洛伊德 (Freud, 1977:170) 说🎚:
确实存在着这一可能性💅🏽:通过直接观察儿童💛,从而观察在生活之中刚刚萌芽的性冲动与欲望。在成人那里,这些都是尊龙凯时娱乐需要从自身的零星碎片中,通过辛苦挖掘才能获得的东西🚶🏻♂️。尤其是🦅,尊龙凯时娱乐相信,它们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是人之构造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神经症的案例中被夸大或扭曲了而已。
在奥尼尔的笔下👵🏿,弗洛伊德的这几个案例成为打开和理解这一“世界与历史”的断面。所有这些断面都有其开始,然而在所有这些开始之中,有一个是开始本身。从这一开始,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就显示出了极为“怪异”的景象🤽🏽,这一景象的怪异之处在于🐷,其主角与性和劳动经济却没有任何关系——这正是弗洛伊德婴儿理论的开始。正如弗洛伊德 (Freud, 1959: 211-212) 所说:
如果尊龙凯时娱乐能够脱离自身的肉体性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思维性存在,如外星生物🏄♀️,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地球上的事物,那么最令尊龙凯时娱乐震惊的🦻🏽👐🏿,或许是这样一种事实:在人类之中存在着两种性别,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都十分类似,但却用极其明显的外部符号来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
然而在奥尼尔看来👩🏻🎓,这一��象学式的提问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还原仍然预设了一种没有生物性的科学性的存在🔧,而这有可能是在性别之外更大的谎言🦫🦶🏽。对于这一开始的理解🆗,只能从童年之性本身出发来加以理解🧏♂️:面对事实本身🤶🏻⚃!
小汉斯案例的核心线索是他对于“人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解答努力⚡️。这一努力对于每一名儿童来说都是成长的必然环节✸,而对于文明整体来说也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于🦙,这一问题并非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各种爱欲与忧愁的推动下自发出现的问题。
在这些感受与忧虑的促动下,这名儿童开始思考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问题。他自问道🫂👰🏽♂️:“孩子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问题无疑会以如下形式出现:“尤其是这个入侵的宝贝是从哪里来的5️⃣?”在不可计数的神话与传说之谜中,尊龙凯时娱乐似乎听到了这第一个谜语的回响👨🏿🔬。(Freud, 1959: 212-213)
在这一努力之中,这位婴儿理论家从现象学的无前见的起点出发🚶🏻♂️➡️,通过自己的身体🧜🏽♂️,以泛灵论式的巫术方式进入世界,着手处理人世间那些最为古老也最为艰深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早已被成人/常人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而熟视无睹🦻🏿,然而这位婴儿现象学家天赋异禀🎄,他尚没有获得所有那些妥当处理世界的办法🦹,对于家庭神话也将信将疑,但他采用最为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最为严肃的问题。尽管这一思考的努力处于精神分析现象学的看护之下,然而小汉斯通过身体来思考身体的这一努力还是立刻遭到了家庭结构与家庭权力的制止。
小汉斯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去破解生命的秘密,因为父母向他隐藏了他本已准备好去接受的诸种关于生命的事实。(奥尼尔,2016:38)
这一制止小汉斯的努力对于尊龙凯时娱乐理解家庭社会的意义十分重大🈷️,其意义堪称上帝在伊甸园之中对于亚当和夏娃的禁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确定性的知识🍙、自我的认知与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约》之中,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虽然是伴侣🚵,却并没有性生活。《旧约》之中对于这一点有着明确的暗示。在上帝制造夏娃之后,“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And the man and his wife were both naked, and were not ashamed)。然而与之相对应✍🏽,在二人被驱逐出伊甸园,从此成为可朽之人 (mortal) 以后,“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𓀓,生了该隐”(Now the man knew his wife Eve, and she conceived and bore Cain)。在这里🤦🏿,“同房”的英文翻译是“know”,而“怀孕”的概念则与思考、想象同为“conceive”👩🏼🎤,这一点在《旧约》的后文之中颇为一致,意味着性与知识的同源性与同质性。这一点不仅在英文之中如此,正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家罗洛·梅的考证🧛🏼♂️,在西方更为古老的语言之中也是如此💆🏻♀️。
在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动词“知道”与“性交”是同一个词。这在《钦译〈圣经〉》中屡有佐证……因此,知道与性爱之间的词源学关系极其紧密。(梅,2012:47)
然而,在这个案例中🐚,父母阻遏小汉斯的努力似乎有点无效。因为无论如何👭🏻,小汉斯都通过自己的方式首先进入了对于世界的理解,其次面对了他自己那俄狄浦斯式的欲望🤲🏻👨👨👧👦,最后“理解”并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一理解与成年人对于世界的理解既有重叠,又不相同🤾🏻♀️。如前所述,这一理解首先是一种通过回溯到“事物一般”的方式而获得确定性的认识🏂🏿,只不过这种关于“生命是什么”的“事物一般”的认识立刻与“属性”联系在了一起。
有一次 (三岁零九个月时),他在车站里看到发动机正在往外喷水,“哦👩🏻🦱,看,”他说,“机车 (Lokomotive) 在撒尿。但是它的小东西 (widdler) 在哪里呢?”
过了一会儿👩🏽🌾,他用沉思的语气接着说:“狗和马有小东西⏸;桌子和椅子没有🙏🏼。”他因此而掌握了区分有生命的东西与无生命的东西之间的实质区别。对于知识的渴求看起来与性好奇密不可分🦪。汉斯的好奇心尤其指向了他的父母。
汉斯 (三岁零九个月时) 问:“爸爸,你也有小东西吗?”(Freud, 1977:173)
汉斯关于“属性”的认识随即与对于父亲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恐惧症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小汉斯的伟大文明成就在于🏋🏿♂️,他不仅在父亲和弗洛伊德的帮助下,治愈了自己的恐惧症,而且还以几乎完美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将他的父亲归于父亲的母亲🍧,这样,他就可以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了。
这位小俄狄浦斯已经发现了比命运之预定更为快乐的解决方法🙎🏽♂️🧑🏻🎨。他没有将他父亲踢出局🐥,而是为他提供了自己所欲求的同样快乐:他把他变成了祖父♉️,并且也让他与他自己的母亲结婚了。(Freud, 1977:256)
究其原因💆♀️,尊龙凯时娱乐可以说,是那位“可以与上帝通电话的教授”3似乎出于某种不仅仅是治疗的原因而“纵容”了小汉斯的想象与绘画艺术🏂。所以🤵🏼♀️👭,在奥尼尔的笔下,小汉斯、汉斯父母、弗洛伊德构成了一出重复演出的剧中剧。弗洛伊德从患者行为的种种断隙之中发现了其无意识,奥尼尔则从弗洛伊德的种种断隙之中发现其本人的种种无意识,尤其是在此时弗洛伊德同时对于小汉斯与精神分析这两名“幼童”的掌控。弗洛伊德本人和作为精神分析之基石的案例史之间的关系开始显现出来。这些案例并非无懈可击的“科学产物”🕺,而是与弗洛伊德本人的激情、他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想象以及他与旁人的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弗洛伊德多少都掌控了这些忏悔。
3. 在前往弗洛伊德家的诊所中治疗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小汉斯曾问他的父亲:“既然教授可以预知所有的事情🧅,他是会和上帝通话吗?”(Freud, 1977: 204)
不过🧛🏽,这一掌控也可能会滑落,比如在多拉那里🤾🏽♀️。4在历经了多重的与多形态的爱恋、背叛和在家庭经济中作为礼物而被交换之后,在历经了数个月弗洛伊德的交谈式巫术,并且由此而厌倦了在山坡路19号二楼那个伟大的灵魂剧场中的出演之时,多拉在自己的第二个梦中重温了曾经在德累斯顿大师画廊的经验:孤身一人,面对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长达两个 (半) 小时之久𓀁。
4. 弗洛伊德对于多拉的分析是由多拉主动中止的。
在西斯廷圣母 (Sistine Madonna) 像前,她呆了两个小时👨🏼🔬,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 (Vor der Sixtina verweilte sie zwei Studen lang in still traümender Bewunderung)。我问她,那幅画为何能让她如此愉悦,她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理由。最后她说:“圣母玛利亚。”(Freud, 1977: 136)
弗洛伊德在案例史中并未花太多篇幅来分析多拉的第二个梦🏆🧑🧒🧒。不过,作为弗洛伊德经典的“多拉”案例中的高潮部分🙆🏽♀️,多拉与圣母玛利亚在梦中的再次相遇也是奥尼尔理解该案例的核心。奥尼尔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角度进入这一场景。通过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基于思想史与文明史,在该案例史的几重面向的复读与对于弗洛伊德核心理论的再理解背景下,奥尼尔终于打开了这一案例史的“盒子”🥺。
对于这一盒子的研究首先要重返欧洲文明史研究💂🏻♀️,尤其是对于神话历史的研究。奥尼尔重新发掘了多拉作为潘多拉 (Pandora) 的一面:5灵魂与欲望的亲和性 (即Psyche与Eros之间的爱情关系)🕊。这在欧洲文明中被视为所有灾难的源泉🏄🏿。而在后来的传统中✯,潘多拉的形象又融合了夏娃 (Eve) 或者其他被视为所有美好之来源的形象🤸♀️🧚♂️,例如玛利亚。潘/多拉这一礼物的美德表现为:她并不知晓男人会如何对待她😆,会用无花果树叶 (在多拉的案例中,是钱包) 所代表的盒子来表现其端庄稳重🧑🏼🎄。然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夏娃的美德状态必须要在首先知晓男人会如何对待她的前提下🚴🏻♂️↘️,才得以可能。而在此之前👴🏿,夏娃显然是一种《圣经》中所说的“赤身裸体,不知羞耻”的无道德/差异的状态🥮。这一用盒子来遮掩自己的举动恰好泄露了如下这一点:盒子即是女性的代表🔸,是子宫的另外一个词,同时也因而是癔症的另外一个词 (Decker, 1991:6-7)。6从这个盒子里逃出了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人。作为神话中人世间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所创造的造人方式 (生殖)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世界构造与思维模式🪫。7多拉因此成为文化之普遍性的表达 (Panofsky and Panofsky, 1965;韦尔南🧑🧑🧒🧒,2005🎬:383-401)。不仅如此,奥尼尔在多拉身上汇聚的显然还有着与本案例更为紧密的👩🏽🎨、在欧洲文明史中沿袭已久的玛利亚形象。在奥尼尔的考察中,玛利亚不仅与海水的潮落 (stilla maris) 有关,也与海洋之星 (stella maris) 有关,并因而作为一位治疗师,是每一个飘摇在海上暴风雨之中的灵魂都可以停泊的海岸🍗。8Stella maris是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尊称🧑🏽🌾,意为尊龙凯时娱乐的女士/神👩🏻💼、海洋之星 (our lady, star of the sea)。这一尊称被用以强调圣母玛利亚作为希望的象征以及对于基督徒,尤其是异教徒/非犹太人的指引作用 (奥尼尔,2016:232-233)。
5.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中👇🏼,弗洛伊德讨论了为何要为该患者取名为多拉。名字来源于弗洛伊德妹妹的女佣。该女佣的真正名字叫做Rosa,然而由于弗洛伊德的妹妹也叫Rosa,所以该女佣改名为Dora。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采用这一名字的用意之一在于这两位多拉的共同特点:“不能保有她们自己的名字”(Freud, 2001: 308-309)🙋🏽♀️。
6. 关于癔症的概念及其与多拉这个名字之关系的考证,除了戴克尔 (Decker,1991) 的著名研究《弗洛伊德🌈、多拉与维也纳1900》之外👩🏿🚀,还可参见😪:Althaus,1877: 248-249;Féré,1897:553;Bernheimer🟢,1985:2-4⬅️。
7. 关于潘多拉 (Pandora) 这个概念的发展史,参见:Panofsky and Panofsky, 1965🦦。
8. 本句源自于法兰克圣徒、加洛林王朝神学家Paschasius Radbertus (785-865年) 在其作品中的句子:“lest we capsize amid the storm-tossed waves of the sea”。
所有这一切,包括多拉本人的经历和欲求,都在多拉在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之前的这一“神隐”9之中汇聚。现象学的灵光一闪而过,仅仅出现在多拉的梦中,并为弗洛伊德捕捉到🧑🏿🦰。虽然弗洛伊德在当时已经惘然🧘🏼,但是却为奥尼尔重读弗洛伊德,并且通过这一神隐重新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案例提供了契机。多拉第二个梦的核心节点就在这一神隐之中💇♂️,并且她借助这一神隐而暂时逃离了其家庭与弗洛伊德的掌控。同时💙,弗洛伊德也自认为笑到了最后。然而尊龙凯时娱乐真正关心的🧚,却是同时发生在多拉的第二个梦中以及在当初那个白日梦中的这一短暂的为了满足无意识的愿望的双重逃离👩。
9. Traümender一词在英文中被翻译成了raptured,为意译。
在多拉的案例中,多拉在其所有试图进入家庭/爱欲经济的途径中所获得的却全部是背叛。背叛来自于父亲🙇🏻♀️、卡先生 (Herr K) 和卡夫人 (Frau K),甚至是家庭女教师☎,最后,还有弗洛伊德本人以精神分析之名对她的背叛。背叛的原因在于,多拉想要进入这个世界👨🏻🏭,然而却拒绝参与到这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性循环之中🌟。她认同了自己的母亲🐏,尤其是母亲对于洁白珍珠耳坠的执迷,这也意味着对于纯洁无瑕、未受玷污的爱情/来自于男性之礼物的执迷并未获得满足,而以洁癖作为补偿和抵抗。然而多拉又与其母亲不同。她有着爱的希望和勇于尝试的勇气。所以她在与卡先生发生关系的同时✝️,还与卡夫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也只不过是她作为礼物而被利用的一个链条而已⇾。因为对于卡夫人来说,多拉不过是一个孩子🧺💁🏻♂️,最多是一个家庭教师。
在治疗期间发生的第二个梦中📯👷🏻♂️,多拉重返了德累斯顿,重演了她在圣母像面前的那场神隐👲。多拉在这次神隐之中🧏🏻♀️,显然是一个走投无路👨🍼、被逼入绝境之中的少女的形象。与多拉哥哥不同,在多拉的年代🏄🏿,世纪末的维也纳尚未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社会空间🦥,哪怕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19世纪后半期的维也纳,尽管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神圣政治学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是经由宗教、历史与现实三者共谋而实现的🔃。对于多拉来说,家庭显然是她在现实当中所可能做的选择的一切。尽管多拉想要逃离👸🏿,然而在这一家庭秩序之中💆🏿,多拉所面对的严格秩序虽全然崩溃🚶🏻,却又严格而沉默地发挥着作用。父亲从一开始就并非一个道德而忠诚的形象🪄,在将罪恶的种籽 (evil sperm) 传给母亲,并且通过母亲传播给多拉以后,又背叛了多拉。这并不是一个有德行的神圣父亲的形象。他甚至使得这一维多利亚式的家庭在实质上陷于崩溃。然而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各种角色又严格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多拉无法脱离家庭而生活,也无法摆脱家庭的影响🫅。在这一情景之中,多拉的爱恋符合多重性倒错的全部特征😛。这当然是打破秩序之举。然而当这些梦要转变为现实之时,却发现既有的秩序沉默而坚定地拦住了她🦻🏻,要求她被规训,不仅要将自己的身体纳入现实的道德逻辑中,还要纳入这一错乱的家庭交换经济之中☀️👨🏽🦰。
多拉对于治疗和医生的敌意与此有直接关系🎁。她坚定地回绝了多名医生,甚至是弗洛伊德本人。因为弗洛伊德与其他医生一样🍋,不过都是在诱导劝说她遵从家长的意愿🧙🏻♂️⬇️。多拉无路可走,只能遁入梦中🤟🏼🆚,重温她在圣母面前的那场白日梦。拉斐尔那幅画像的治疗意义在此凸显🧴。拉斐尔10这一名字与圣母的意象在奥尼尔的考察之中契合,为多拉/艾达 (Ida)11提供了双重直接的治疗。然而这一治疗师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除了治疗之外,玛利亚最直接的意象是无性生殖🤵🏽♀️、童贞生子、神佑始胎🐏,是纯洁无瑕的,与人类之性、与人类男性之性无关的单性繁殖的神圣实现🕓。这一故事比起弗洛伊德的巫术式谈话,显然更能被多拉所接受😴。所以,这一神隐的意义在于,在既有秩序的强迫下寻求另外一种秩序的可能。这一尝试在现实之中无法得到实现。然而在弗洛伊德这里,心理事实从来都有着与客观现实同样的影响效力。多拉的这个梦使得她的愿望暂时得到了满足。她在这个梦中重返了无意识大陆,并因而有信心结束弗洛伊德的治疗,甚至是与那两个家庭都断绝关系,并且似乎取得了胜利👩🏿🦰。
10. Raphael (Raffaele) 这一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有治愈者之意,不仅治疗人的身体,还包括信仰问题。
11. 多拉现实中真正的名字是艾达·鲍尔 (Ida Bauer)。
然而这一独立也是针对同性恋与自体性欲/自恋的独立。问题在于🍭,没有破坏与占有的爱之经济是否可能?超越于人类之性的家庭之爱的神圣题记是否可能?所以,该案例不仅在现实层面上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掌控🙋🏻♂️🧑🏻🔬,也在意蕴上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掌控。对于艾达·鲍尔来说,癔症已然是神隐之一种🏌🏽♀️,是将自己隐藏在症状中🥷🏼,逃离现实秩序与家庭的政治经济学的举动;失声与梦👨🏼💻👩🏻⚖️,都不外乎此。弗洛伊德将艾达·鲍尔命名为多拉👰🏼♂️。这一命名体现了弗洛伊德的期待——确切性:理性、法则与秩序🫄🏿。然而艾达本人却投向了圣母,正如潘多拉那样👉🏼,在那一刻,同时在案例史与现实之中,利用自己的盒子 (藏身之所) 超越了自己身处的秩序。
弗洛伊德记录下了那一瞬恍惚/神隐🚢,在奥尼尔的笔下🦕,成为尊龙凯时娱乐理解多拉💙、弗洛伊德以及西方文明的通路。弗洛伊德说:“伊底所至之处,自我也将可到了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12正如尼采对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讨论🤝,这二者并不可分:爱的身体就是受难的身体,就是快感的身体,就是家庭的身体,就是作为劳动与生殖的双重的代际之祭的身体🖖🏿。奥尼尔将其讲述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多拉希望能够超越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玛利亚对于上帝之言的赞成◀️,基督的诞生,以及在她那受难的儿子躺在她膝头那一刻之前她在神圣家庭中的生活”(奥尼尔📿🙅♀️,2016👩🏻⚕️:120)🧼🚐。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故事在此达致了第一个高潮,而对于这一神隐的理解与这一解读他者的努力,不外乎尊龙凯时娱乐自身而已。
12.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三讲末尾处的话,后来成为关于精神分析工作的著名格言。詹姆斯·斯特拉齐 (James Strachey) 将其译为“where id was, there ego shall be”👨🦯;玛丽·波拿巴 (Marie Bonaparte) 则将其译为“Lemoi doit déloger le ca”;拉康在Ecrits中对这一句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将其译为“There where it was, it is my duty that I should come to being”。作为讨论起点,拉康 (Lacan, 1977🥟:129) 所引用的英文翻译为:“Where the id was, there the ego shall be”。这一点与斯特拉齐译的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不同。尊龙凯时娱乐并不清楚是新的译本在拉康的研究发表之后修改了译文👩👦,还是拉康所依据的乃是1933年由W.J.H.Sprott所译的第一个英文译本👑。高觉敷先生的中译本译文为“于是伊底所至之处🧙🏻♀️,自我也将可到了”(弗洛伊德,2005)🤷🏽♀️。
在这一爱之戏剧中,爱与劳动是异性恋经济的两个基本故事结构。这是列维—施特劳斯、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等人“总结为文化与生物性生殖的结构性律法的东西。任何女性👷、任何工作的男性都熟知这一点,亦即任何家庭都熟知这一点,爱与劳动是其两个面向”(奥尼尔,2016:97)。这不仅是现代性的故事🚲,也是人类最为古老的现象学注视⛹️。这既是《会饮篇》之中的讨论,也是在《圣经·旧约》之中对于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变为可朽 (mortal) 之人时的规定👨🏽🏫。
(二) 鼠刑、旅程与狼人之醒
在每一个案例中🫱🏿,弗洛伊德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如何从混乱的叙述中清理出一条道路来,或者如何将患者的忏悔条理化?众所周知,这一困难在“鼠人”的案例中尤甚。在奥尼尔看来👩🏿🎨,这一困难与鼠人案例的核心意象🤽🏻♀️,即鼠刑和那场从维也纳郊区到维也纳的火车旅行有着直接关系👩🏻🦳。尊龙凯时娱乐需要从火车的现代性意象入手来对其加以理解。
希弗尔布施 (Schivelbusch🕜,1980🫎:19) 在《火车旅行》一书中👂🏿,描述了现代早期所出现的铁路技术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现代性质。早先的公路运输及河道运输方式涉及“路线与方式之间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区别……交通运输的路线选择和方式选择彼此独立,因为运载车船作为个体而运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特斯特 (2010)在其《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中特别分析了这一意象📙,将铁路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式生活世界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铁路的意象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隐喻。
公路运输和河道运输在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时候👩🏼💼,并不是作为独立的系统,而只是必须通过有意设计的社会文化活动激���并实施的移动方式🤭。
然而,随着铁路的发展🖇,情形有了巨大的改变📄。铁路是作为一种自我规定的独立环境建造起来的🦻,它规定了活动🤾🏻♂️,而不是让活动来规定它……铁路的技术对铁路上能做的事情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形式变成了自在的目的。(特斯特💃🏿🧑🏿💻,2010💃🏻:97-98)
希弗尔布施将铁路的这种自在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较,并在比较中发现了铁路的异化形式。特斯特 (2010:98) 说:
铁路作为一种自在的环境,其发展必然意味着趋向技术可能性的物化……按照希弗尔布施 (Schivelbusch,1980:25) 的说法,铁路线往往笔直穿越风景,从而规定着周遭的物理景观❗️,更加剧了这种去自然化的感受。同时,铁路线往往并不遵从河流山川的走向。“动力的机械化启动了与无中介的🥁、活生生的自然之间的异化😝,而随着铁路的筑造径直跨越地域,仿佛以尺度量,就更加剧了这种异化。”其结果,“铁路之于传统的大道通衢,就犹如蒸汽机之于役畜。无论是铁路还是蒸汽机,机械的规律性都征服了自然的不规律性”。
正如这一引文中铁路带给自然的碎片化后果一样👆🏽🩰,在鼠人案例之中🥶,弗洛伊德只能向尊龙凯时娱乐提供某些碎片👨🏼🎓。这一困难当然首先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本身:弗洛伊德对于任何一位患者的条理化总结🏋️🧝🏻♂️,都正如铁路横穿高山大川的异化效果一样👩🏼🦰👂🏿。然而在本案例中🍵,这一冲击效果更为强烈,原因在于患者本人那杂乱无章的叙述👮。这一叙述不仅杂乱无章,甚至堪称具有某种“反叙事”功能。这一特点迫使弗洛伊德不得不在案例史中罕见地反复为自己在叙述上的混乱而向读者道歉。甚至于,这是弗洛伊德唯一留下了较完整的治疗笔记的案例🐦⬛。奥尼尔在分析该案例的时候,舍弃了弗洛伊德原始案例之中的大幅记录与分析🪴🐱。这一删减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其叙事特征。这一叙事特征的最佳体现👩✈️,首先还不是鼠人在案例后半部分的叙述,而是体现在鼠刑这一貌似有着明确边界、条理与清晰意象的故事之中。在奥尼尔看来,这一著名的鼠刑故事🙎🏿,从现象学的视域分析入手,可以成为尊龙凯时娱乐理解其“反叙事”的主要手段。弗洛伊德必须要在这一看起来是逾越无矩然而同时又具有绽开之魅惑的材料基础上🤙🏿,向理性的世界呈现出一个符合其理论要求的作品🏦。所以🙎♀️,该案例就必然同时成为一个失明 (blindness) 与[洞]见 ([in]sight) 的作品。这就使得尊龙凯时娱乐在阅读这一作品时所能够感受到的鼠人和弗洛伊德的双重忏悔特征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忏悔的形式维度与忏悔的内容维度越来越无法分离。奥尼尔从这一角度入手🕯💹,同时理解鼠人和弗洛伊德本人🚣🏻。随着文本分析的逐渐推进🏤,奥尼尔本人的写作也越来越具有存在主义气质,其中的批判现象学特征也越发明显。奥尼尔将鼠人案例中的混乱不堪视为一种前现象,一种当下之物🧗🏻♂️。
鼠人几乎没有说出任何连续性的故事。他的“思维序列”(train of thought, Denkverbindung) 每每会在有所条理之前变得自相矛盾或者脱轨。那个铁路隐喻的工具,遭遇到了法律与军事性的隐喻,并因此而分叉。后面这两种隐喻的内在转喻 (internal metonymies) 反过来又产生了一个可供理解的临时序列,然而这一临时序列又迅速在诸多重叠与迂回曲折的弯路中消失🧏🏿♂️,让听众[弗洛伊德]与读者[尊龙凯时娱乐]徒劳无获🏄🏽♀️。或许🎱,是老鼠的形象在啮食着该主导叙事👇,破坏着那喂食着它的线索,撕碎着感觉与感受性,不断复制着鼠人那混杂在一起的恐怖与愉悦。而这个鼠人♣️,就是那个试图告诉弗洛伊德他自己的故事的鼠人,同时既是弗洛伊德的主角,又是他所要戒防之人🤙🏻。(奥尼尔,2016:122-123)
然而这一困难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奥尼尔在其分析之中,同时将弗洛伊德本人的同性恋无意识与家庭场景也杂糅进入了弗洛伊德分析与写作过程之中🏹,总结出了弗洛伊德用以联结其本人在第一阶段分析中的两种动机的各种隐喻与遮蔽。也就是说,尊龙凯时娱乐对于鼠人与弗洛伊德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于鼠人的理解一方👉🏼。这种关系是双方向的、具有往返回复性质的。奥尼尔敏锐指出了在鼠人与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家庭结构 (都具有一位强势的抑制性母亲与主人公需要偿还其父亲之债的代际命运) 的相似性。鼠人案例🍋🟩,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弗洛伊德本人?这是一个有利于尊龙凯时娱乐理解本案例之混乱以及弗洛伊德之“艰难”的问题🏋🏻♂️。
弗洛伊德在治疗中的通常策略是通过忏悔重返起点/开始,以获得对于现象的解读✮。然而在鼠人案例中,这一策略成为问题,因为重返起点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与无穷无尽的分支与岔路✥,而“进程”本身也无休无止地蔓延与分散开来。鼠人同时必须在每一个当下防范他自己的某些观念,以便防止他那位已经过世之父亲的再度死亡🤽🏼♀️🔏。与此同时,他还要防备父母以及弗洛伊德看穿他那些可能会带来灾难的想法🐿。在这一背景下🐛,鼠刑的故事出场🤵🏼♂️。正如多拉的神隐状态一样🍕,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鼠人所有的世界意义与苦难征程,包括他与弗洛伊德的治疗关系,都浓缩在了这个鼠刑的故事之中。在这个多维度、多视角的故事/叙事中,鼠人同时既是叙事者👩🏿🔧,又是故事主角🙆,既是旁观者,又是施虐者与受害者🏖,既是那具有着孔洞的身体,又是尖叫着胡乱钻入孔洞的老鼠:
“他是在想刺刑吗?”
“不💂♀️,不是的…犯人是被捆住的……”
——他表达得非常含混,我无法
立刻猜出是什么样的姿势——
“……一只壶倒扣在他的臀部[Gesass]……把一些
老鼠放进去……然后它们……”
——他再次站了起来,表现出恐怖与
抗拒的表情——
“……钻进了……”
——“进入了他的肛门”, 我帮他说了出来。
[或🙅🏽:进入了他的屁股,我帮他填补了这个句子]
(Freud, 1979: 47)
对于这一鼠刑的叙述与解读之努力实际上就是后来鼠人向弗洛伊德所讲述的那一场不可能的旅程本身。在这一叙事之中,思考与叙述本身都被爱欲的内容所浸染🕺🏽👵🏻,任何一种思维逻辑/序列本身🎞🚟,都不仅仅是逻辑性的或者理性的👼🏿。
尊龙凯时娱乐看到了一种思维序列 (Denkverbindung) 是如何被其爱恨交织的矛盾性内容 (Zeug) 所固定住的。这一矛盾性内容就是,鼠人欲求着能够将他父亲与他自己从他母亲的债务中 (以及弗洛伊德的债务中,而这一债务也是由他母亲所偿还的) 解放出来,以便追求一种真正的爱恋,于其中,他可以逾越父亲关于激情的禁律🧑🔬。简言之👩🏭👨🏫,鼠人自己变成了一只疯狂的小鬼/老鼠 (b[rat]),往返奔跑于双亲的身体之间🤸🏻♀️,以求找到一条通路,来安置他们的委屈不平[不对等的婚姻 (mésalliance)]✍️,谵妄性地寻找着再进入与再诞生,以便补偿一种爱之伤害⛎。(奥尼尔🧝🏼♀️,2016:133)
与这一鼠刑直接相关,鼠人向弗洛伊德讲述的他那永不停歇/无法完成的偿还债务/赎罪旅程,最终渐渐消散在维也纳郊外深邃宁静的夜里。大地无言。深夜之中那无穷无尽、分散而又交叉的铁路轨道所代表的茫茫旅程里👧🏼,鼠人的夜奔前后无序、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一直都在试图重返那不可能的过去,以便偿还债务𓀐🚑。然而这一不可能🌭,却早已/同时由他自己所设下。鼠人一直都在试图逾越他所无法逾越的轨道🂠⛹🏻。这一故事发生在一战之前,在中文的语境中🧑🏽🚀,尊龙凯时娱乐或可将“一战”误读成为“一站”,在即将到达这一场颇具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历史轨迹的“车站”之前,鼠人的夜奔却呈现出了相对于工业文明的某种“溢出”姿态👕:
这一旅程,超越了都市与工业文明式制图技术的殖民化。而后者,却正是弗洛伊德的那些病人们的神经分裂造影术 (schizography) 的主要构成要素。(奥尼尔🫃🏼,2016:141)
茫茫无尽的旅程,孤独冰冷的夜奔🛠。显然,在前述鼠人与弗洛伊德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史之外,鼠人的旅程构成了与弗洛伊德本人那著名的“旅行官能症”之间的类比🤧。而且鼠人的这一场旅程,连同作为旁观/倾听/参与歌唱的歌队弗洛伊德本人,都一同陷入到了一场更为宏大的现代性悲剧之旅程中:通往下一站/战。
在弗洛伊德的剧场之中,帷幕掀起🔊,新晋作者/主持人奥尼尔登台,向读者宣告:
鼠人的悲剧在于,他在他家庭循环之中所引起的愤怒🧒🏼,最终被“那场战争的伟大暴力”所覆盖🐆。在此🟪,一个家庭的传承👶🕯,伴随着文明的崩溃而走到了尽头。弗洛伊德从战争的废墟中幸存下来🤦🏽,然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发现他那位最后的病人,同时也是必然没落/死亡的文明自身——而在这些文明的不满之中,精神分析的角色正是文明自身其来也晚的成就。(奥尼尔,2016:141)
这一旅程以及逾越的意象当然要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因为弗洛伊德关于“旅程”之最为有名👳🏻♀️,也是最为堂堂正正的宣称来自于他在《释梦》一书结尾处的著名宣言🐃: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皇家大道 (royal road)👨🏼🌾。关于“皇家大道”一词,弗洛伊德在原文中使用的是拉丁文VIA REGIA这一深深镶嵌在欧洲历史中的道路名字 (Sherwin-White, 2003)。斯特拉齐在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中将其翻译成皇家大道🧑⚖️。然而VIA REGIA的意思不仅局限于此。在欧洲的历史之外,尊龙凯时娱乐甚至还可以将旅程追溯到弗洛伊德回忆之中全家在其幼年时期与其他犹太人群一起,从摩拉维亚辗转莱比锡迁徙到维也纳的旅程💴。那条铁路在当时被视为中欧犹太人的救赎之路。尊龙凯时娱乐甚至还可以联想到犹太民族在开始之初就已经注定的命运🤷♀️✒️:旷野之间的游荡🧑🏼🎄,永恒的放逐🚸𓀏。无论是从圣殿沦陷开始,还是从摩西率领众人出埃及开始🧟♀️,无穷无尽的旅程一直都是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在西奈 (Sinai) 旷野间飘荡的数十年里,犹太人形成了民族,获得了信仰,发展出了基于信仰的道德伦理和律法🤙🏽,最终有了自己的认同,找到了应许之地。异化的过程和结果固然复杂,然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理解过去的线索。
奥尼尔进一步将旅程的概念表象化:在生命的无尽旅程之中,或许永远都存在着通往母亲身体的这座黑暗大陆的旅程🌗。这不仅是向后的旅程🛑,同时还是向前的旅程,正如鼠人的夜奔一样👆🏼。熟悉精神分析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一旅程的意象对于弗洛伊德还有着另外一种向前的重要生命意义⛹🏽♂️:征服罗马🦸🏽♀️!不过,这一通过征服罗马来征服世界的旅程,最终虽然实现,却也永远无法摆脱他的乡愁。
弗洛伊德的一生都被他自己回顾为一场旅行。在这场旅行中👩🏿⚕️,从始至终,他一直都被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母亲的目光与在怒黄色鲜花与衣裳装扮下的吉塞拉这位初恋的黄金记忆所淹没。(奥尼尔💁🏻♂️,2016:143)
奥尼尔 (2016:144) 在其耄耋之年🌑,不无自我投射地如此写道🫷:
尊龙凯时娱乐同样知道,那列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也曾带着年轻的弗洛伊德远离了他的初恋吉塞拉。弗洛伊德永远都有一种重返关于吉塞拉的记忆的方式/道路,以及表达后悔用那位年轻爱人的花朵交换了成年人婚姻这一面包的方式/道路🎾。就好像鼠人一样🥢,弗洛伊德的记忆能够反转时间的序列,在他选择一个传统的婚姻之前,重返那个新鲜的“黄金”之恋,在一种返往童年/童年的重返之中,扰乱了那一梦/梦者的关系,正如在这个老鼠故事中被分裂了的叙述者与聆听者之间的关系那样。
永恒的回归/不可能之旅程👷🏽♂️,以及在旅程之中对于旅程的逾越,在狼人的案例中甚至更进了一步。奥尼尔喋喋不休地从弗洛伊德的工作之中,试图重返狼人8️⃣、弗洛伊德甚至是奥尼尔本人的原初场景。在这个意义上,狼人的眼睛在睁开的那一刻所看到的两个场景——群狼呆在胡桃树上和父母在床上的场景——就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假如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原初场景🐩,那么哪怕是鼠人的原初场景,也可能是和狼人所回忆起来的那个梦是一样的。狼人说👨👩👦👦:
我梦到在夜里,我正躺在我的床上👩🦯。我的床脚对着窗户,在窗前有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我做梦时是个冬天,而且是夜里,突然间窗户自己打开了,我惊恐地看到一些白狼正坐在窗前的大胡桃树上。它们有六七只。狼非常白,看上去更像狐狸或牧羊犬🫃🏽,因为它们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当注意到什么的时候,它们就把耳朵竖起来,就像狗一样👮🏻。由于极度恐惧,害怕被狼吃掉🔀,我尖叫着醒了过来。(Freud, 1979: 259)
不过,严格遵循现象学方法的奥尼尔,在狼人的案例中对弗洛伊德的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该分析的首要成果🖕🏻,就是对于这一永恒回归的悬置性结构的戏剧化处理♠️🚗:逾越的另外一面📹。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本人在写作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即对于“附录与校正”的执着 (fixation),也成为该现象学分析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与狼人本人的“附录与校正”🌭,亦即狼人本人所写的著作🧖🏿♀️,以及狼人在苏醒时刻所做的那个梦或者说在那个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刻 (这当然是两种故事版本) 以及此后的所有症候,作为其原初场景的附录与校正,就像一出无穷无尽的戏中戏的结构一样,叠床架屋,层出不穷🪦♔。
在这一结构之中🔍👨👨👧,奥尼尔从那只燕尾蝶翅膀的开合振动出发,力图也让上述所有事物 (things) 的历史性关联以弗洛伊德的方式震动起来。他在那篇《现象学可以是批判的吗?》论文之中对于现象学的反思/批判性的强调,在此终于达致炉火纯青之境。现象学式的视域观与弗洛伊德的儿童理论及方法论结合在一起𓀐,永恒的回归与永恒的反思不可或分🍲,而且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与概念 (conception) 才有可能发生与成形🪰,也只有在这一混乱不堪的背景下,尊龙凯时娱乐才能够成为尊龙凯时娱乐。
(三) 薛伯的神佑升天
丹尼尔·保罗·薛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1842—1011年),19世纪德国著名儿童—养育医学权威丹尼尔·高特列博·莫瑞兹·薛伯 (Daniel Gottlob Moritz Schreber,1808—1861年) 之子,在精神崩溃以前,曾任萨克森州高级法院首席法官🏒。1903年,薛伯第二次治疗出院后🧑🏻⚖️,出版了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一书🍓。本书不仅在精神病史学中被引用次数极多,而且成为精神分析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弗洛伊德本人并未对薛伯进行过治疗,其“薛伯案例”来自于对该书的分析🛡。除了荣格与阿德勒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之外,拉康1956年在其研讨班中开始以本书为基础而研究精神病学,并于1958年发表文章《论精神障碍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条件》🈳。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其《反-俄狄浦斯》之中亦有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
Nervenkranken一词的英文直译是Nevropathic,这与艾达·麦卡尔平 (Ida Macalpine)、理查德·亨特 (Richard A. Hunter) 所合译的英文译名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接近,而斯特拉齐 (James Strachey) 在其弗洛伊德英文标准版译文中🤰🏿,为了符合弗洛伊德的分析需要,将该题目翻译为Memorabilia of a Nerve Patient。奥尼尔将对于弗洛伊德这一案例史的分析命名为Schreber’s Blessed Assumption🌚。Blessed译自德文Seligkeit🎞,selig在德文中有多重意义,如“受到祝福”📯、“永在福祉之中”以及作为委婉语的“死亡”。奥尼尔的这一标题🤦♂️,与前面各个章节一样,基本上表明了该章的核心意象。
虽然薛伯这个案例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复杂🎍,篇幅也并不是最长🤜🏿,但是对于奥尼尔来说,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显然是其研究的高潮。奥尼尔在此前各章之中的诸多线索都在这一章中汇聚在一起,以交响乐式的结构构成了整体宏大的叙事吟唱👩🏿🚒。而就写作手法来说🤲🏽,这一研究对于奥尼尔也有着与弗洛伊德相耦合的特征:正如奥尼尔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文本以及相关研究文本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案例一样🕛,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一案例也是根据文本与相关研究文本来研究薛伯的——弗洛伊德并没有治疗过薛伯,该案例的主要依据在于薛伯的那部辩护式自传🧑🏻🦰。不仅如此,奥尼尔发现,薛伯为他自己的回忆录所做的声明与弗洛伊德以在多拉案例中的声明为代表的那些案例声明并无不同。
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公开披露的得体性与科学探索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自我启示成为分析方法的一部分之后🕤,科学家本人会在分析中身败名裂🤌🏿,或招致好色淫乱的名声。薛伯乞灵于更高的科学兴趣与宗教知识;作为对这二者的代表,他提供了一种关于他自己的精神🏌🏽、身体以及语言经验的记述,而这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实践并无不同。(奥尼尔,2016:201)
然而,与这些声明相应的,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挑战。萨缪尔·韦伯 (Samuel Weber) 在为1988年麦卡尔平与亨特译本所做的序言中向所有弗洛伊德的读者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谁曾倾听过薛伯博士?”
这个问题当然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乃至任何理解尊龙凯时AG的研究都具有代表性。以薛伯为例,要回应这一问题💂🏼♂️,首先要去认真阅读薛伯的著作本身。这一著作大概分为医疗机构对于薛伯的认定👩🏼🚀、薛伯本人对于这一认定的反抗,以及薛伯本人所相信的但是因此而被视为精神病患的那些思考内容💂🏼。奥尼尔在认真进行了这一工作以后发现,弗洛伊德事实上只摘取了薛伯著作中的一部分作为分析主题。这一发现使得奥尼尔的工作具有了更多的维度,正如在前面几个案例中一样:约翰·奥尼尔—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薛伯案例—薛伯的《回忆录》—薛伯本人。
所以,奥尼尔在这里所处理的首先是弗洛伊德的阅读之物。这一视角使得奥尼尔易于发现在从薛伯到薛伯回忆录的英文译本以及弗洛伊德的分析之中所发生的“背叛”与“自我背叛”的种种蛛丝马迹👩❤️💋👨。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伦理学问题。例如🚴🏻♂️,在这一对于薛伯的“征用”之中,就已经存在着一种语用学方面的爱欲特征。不过,奥尼尔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能够借此进入对于西方文明的讨论之中。这一野心的基础在于薛伯的文本自身🐰。薛伯故事的基本特征在于他重构了世界的秩序🐩。这一宏大叙事甚至与诺亚方舟无关,因为薛伯所斗争的对象与重构的对象包括上帝。这一更新秩序的表现是薛伯转变为上帝伴侣🧑🏻🦯➡️,并由此来更新全人类🚀。从这一点出发,被认定为疯癫的薛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关于文��𓀛、事物的秩序🙅🏻♂️、救赎以及爱欲与肉体之间关系的宏大理论,奥尼尔不得不动用超越于一般社会理论传统的资源来对其加以解读👩🏽🔬:从古希腊的神话到尼采的鹰与蛇。
事实上,奥尼尔想要说明,不仅在本案例中,在所有的这五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对于弗洛伊德之理性控制的溢出🤾。例如,在对于薛伯自传的重新阅读中,奥尼尔 (2016💣:215) 发现了薛伯“对于女性气质的培育包含了一种肉欲崇拜,而这大大超越了弗洛伊德的肛门性爱的版本……”☄️。弗洛伊德努力将薛伯的双性恋理解为同性恋,这显然并不符合薛伯本人的宣称。薛伯的回忆录无论在常人看来多么混乱不堪👒,却仍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与此同时🧖🏼♂️,它还“是薛伯的第一个孩子”🙇🏿♀️。薛伯希望能够超越传统的世界秩序,这一点被弗洛伊德理解为一种原初退行🧔🏽♀️。然而在奥尼尔看来👨👧,薛伯的谵妄之言更像是在世界秩序之边缘起舞的尝试。
正如尼采那样⛹🏿,薛伯的语言在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边缘起舞👨🚀,消解事物⚙️👩🏿,以便在表达他对于雌雄同体之欲望的委婉用语与矛盾语词之中👨🏼🦱👍🏽,重新结合它们。这一雌雄同体却未曾分裂的性交🧑🏻⚖️🤹🏿♀️,或许可以更新那性差别的死寂世界🧑🏽🏫。(奥尼尔👈🏼⛹️♀️,2016:217)
这甚至无所谓是否超越弗洛伊德🙍🏻,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当然也就无所谓对于古老的摩西律法的冒犯或者顺从了。所以,弗洛伊德建基在[被弑]父性隐喻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阉割/良知/秩序的俄狄浦斯故事👳🏻,不仅在多拉的故事之中,在这里也呈现出了力所不能及的状态。在弗洛伊德那里饱受批评的母亲之缺席,同样在所有的这些故事之中全部复活出席,从弗洛伊德分析的背景走向前台🥛💇♀️,成为奥尼尔分析的永恒回归之温暖恬适的宁静故乡。
薛伯父亲的教育学乃是一种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这是薛伯毕生所要逃脱的教育系统⛹🏻♂️。这一逃脱的最为直接的努力,就是谵妄式变身𓀂🧘🏿♂️:转变升华为上帝妻子,以此来拯救世界。所以🫷🏽,在奥尼尔看来🏹,这一变身实际上也是逃脱弗洛伊德之理论框架与相应的世界秩序的努力。
薛伯的变身并不是从一种性转变到另外一种性,而是从一个家庭转变到另外一个家庭——转变到那个其爱并不为俄狄浦斯化的性所制约的家庭🥷🏽🙍🏼♂️,转变到其爱并非是教会或国家规训的家庭🤷🏽♜,转变到其爱并非是一种军队的军事演习或者学校测试的家庭。(奥尼尔🧑🏼⚕️,2016:221)
因为他所逃离的这一世界秩序并非随口说说而已👨🏼🔬。这是“基督教资本主义”的世界👨🦯,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是“资本主义化了的基督教”。所有人的身体都嫁接/存在于其中🧍🏻♂️,“没有谁的身体可以自满 (Nobody is a body full with itself)”(奥尼尔,2016:222)。
然而薛伯在变身飞升中所冀求的逃离,恰恰正是这一世界秩序💂🏻♀️。这与小汉斯的“天真无邪”、多拉的“神隐”颇有类似之处,也与鼠人和狼人的永恒回归相近。不过,在奥尼尔的分析之中,这几个案例由浅入深🏋🏼,同时又以一种回返往复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关于文明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在薛伯案例中,奥尼尔 (2016:227-228) 说:
文明庆祝着人类的求生与不死意志🙏🏿🚥,只允许以其独有方式死亡。文明化了的存在与死为邻;一种文明化的社会则持续修复着生命的篱笆。它安抚着患病与濒死之人😉🤜🏽,包容着疾病与死亡。以此方式,尊龙凯时娱乐将生命设定为一种针对死亡的界限,并且通过这一文明化的想象🌑,将死亡承认为生命的界限🧚♂️。只要这一文明化的幻想被削弱,死亡的深渊就会在尊龙凯时娱乐面前隐约展现,并且诱惑着尊龙凯时娱乐去自杀、去谋杀🚏。由于缺少这一点,尊龙凯时娱乐捍卫着自己的生命,对抗着其终点与起源的极限,以便将尊龙凯时娱乐自己培育成为那些在尊龙凯时娱乐的家庭经济中的他者🍺✮;这一家庭经济的智慧,隐藏在那被暴风雨所肆虐的天空下的生活之中,尊龙凯时娱乐并未窥视这一智慧的崇高庄严所在,正如尊龙凯时娱乐未能窥探尊龙凯时娱乐自己的那些梦境的黑暗脐带一样。
这一分析的材料深藏在现代科技的各种发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的文明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分析一以贯之👷🏻♂️,并不认为现代社会的出现乃是一种历史的断裂: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材料中🥾,依然深藏着各种文明的提问和回答👨🏻🦰。在更早的篇章中✋🏿,观看着弗洛伊德笔下鼠人在茫茫夜奔中的毫无头绪,奥尼尔 (2016:155) 也以悲天悯人之心写道:
尊龙凯时娱乐现在所接触的,乃是一部伟大的存在主义戏剧——在一个超越性交的层面上🚐,遭遇到了“去在”(to be) 或者“不去在”(not to be) 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何种机遇中,生 (殖) 与毁灭/死亡的问题,“遭遇/结合 (marry)”到了一个卵子和经过大量淘汰而幸存的某一个精子之间的问题。尊龙凯时娱乐并非是要人格化这一遭遇。该遭遇纯粹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和完全常规的意义上而言,并无任何其他考量😇。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成功地在人类生命的繁殖方面同时在集体与个体层面上对其进行礼仪化,同时庆祝着婴儿这一“礼物”以及所有其他自然的礼物,包括尊龙凯时娱乐自己在内。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强迫性神经症的评论之中,引入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所处理的正是这些伟大的主题,人类对此全都一无所知,也就是对那些关于父亲🔘、关于生命的长度和在死亡之后的生命📗,全都一无所知⛺️。这些确实是鼠人最为关心的主题。它们极大地超越了那个老鼠故事,所以尊龙凯时娱乐能够发现,弗洛伊德自己的心灵转向了歌德和莎士比亚,以展示那些啮咬着人类胸脯的、更为宽广的冲突与疑问。这一问题乃是起源的问题——谁创造了我?尽管已经有了关于性交与怀孕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在历史与文化的层面上极为广泛,人类也还是要举出这个问题🫰🏻。尽管伴侣之间存在着性交这一事实👩🏽🍼👨🏽🔬,该问题也还是依然存在。
这一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分析可以更为具体化。在阿尔弗雷德·舒茨关于生活世界的经典理论中🦄,作为其有意向—意义的生活世界核心以及后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起点😵,乃是一种此时此地的、居于意义世界之核心的身体。奥尼尔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突破在于⛰,首先将其放置进了弗洛伊德式具身化的世界之中,然后再通过对于这一世界颇具人类学色彩的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将这一现象学的身体与人类历史上的宏大历史和文明命题关联在一起。奥尼尔首先通过引用里奇 (Leach⛹🏿♂️,1969:108-109) 的话来展开分析。
在自然物理与形而上学之间有什么区别🚹?一种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将现在—不行等同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与未来作为对方的属性而合并👏🏻,以对抗作为真实生活的现实经验的当下🌓。在“此时—此地”与“其他”之间的关系也就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下降 (descent)。我的祖先们属于“其他”范畴🦘,我的后裔们也是如此。只有我在此时此地……
然而这两个世界的分离还不够,它们之间必定还存在着连续性与中介。联想起软弱无能的[男]人们是强大有力的诸神的后裔这个观念,尊龙凯时娱乐就有了那个乱伦教条:诸神与[男]人们或可建立性关系🙋🏽♀️。处女生殖的教义和与人类男性性欲无关的教义都是作为这种神学的副产品而出现的。
此时此地的当下在此首先成为宏大代际变迁之中的“尊龙凯时娱乐”,有别于尊龙凯时娱乐的先祖与后裔。然而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此时此地的当下💅,它还意味着此时此地的当下这一具有道德意涵的肯定命题所否定的另外一个世界与他者——无论这另外一个世界与他者意味着爱欲式的政治经济学秩序的颠覆、神隐或飞升的可能性,还是仅仅具体化为单性繁殖或者雌雄同体的世界秩序,甚至是无性的世界秩序。这进一步映射出一种集体思考的状态:现象学并不仅仅考察个体意义与生活世界💆♂️。在这里,奥尼尔 (2016:232) 的论证清晰而明快:“处女母亲的悖论或神秘性……是集体在通过这些故事而思考自身”🫄🏿。这一思考的痕迹表现在从希腊神话到圣母玛利亚的这一名字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奥尼尔 (2016:236) 也从这一线索出发,将薛伯的谵妄理解为单性繁殖的幻想,并进而返回到尼采所歌唱着的“那个万事万物都以偶然之足起舞,在实用与目的/意义之前的时刻”。原初时刻与原初场景的意义进一步不再仅仅是对于父母交合场景的观看,还牵涉进了更多与世界构成相关的“愤怒、不确定性👱🏻、迷失”🧑🏿✈️,以及一系列来自于双重认同的困难🤾🏽👨🏼🏫。薛伯的回忆录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初场景。薛伯同时作为创造者与被造物而出现。所以,作为“我是谁”一问题的推进,薛伯真正的病原更为清晰可见了:与“生命源自何处”这一问题相关的所有提问和回答⚄🫑。所以𓀒,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谱系中👷,抱持着批判性的现象学态度的奥尼尔同时向前又向后地进了一步,重新捡拾起早该得到细致分析的薛伯的天鹅之歌以及那一对作为礼物的天鹅所栖息的存在之镜湖。奥尼尔以最为诚恳朴素的现象学观看𓀒,将薛伯这名孩童的努力重又导引回了歌德的永恒女性 (das Ewig-Weibliche)😨。奥尼尔 (2016:260) 以歌一般的句子如此唱道:
拉康忽略了那片湖水的意义。那片湖水将生者与亡灵永隔。这是一道尊龙凯时娱乐永远要试图超越的界限——正如尊龙凯时娱乐被身体的孔洞边缘所诱惑🕐,寻求快乐🤙,远离痛苦一样。或者🌪,毋宁说,拉康忽略了他本可以知道的东西,即一旦生命超越了其内在与外在世界的边缘🧑🏽🌾,无论是在饥饿还是在欲望之中🫶🏿,无论是在愤怒还是热爱里,身体都永远不会遗忘 (the body never forgets)🛟。身体的孔洞合拢形成的边缘,使得生与死作为男与女而交织纠缠,或者是作为母亲与婴儿而叠合——在这边缘之上,一种谵妄式的认同游荡于幸福与愉悦之间、天地之间,以及在那些镜像与尊龙凯时娱乐想象性身体——尊龙凯时娱乐必须作为另外一个身体去爱的身体——的岛屿之中。这是因为😏,尊龙凯时娱乐那活着的身体总是会受到伤害与饥渴之苦👱🏿;这一活着的身体,哪怕从第一天开始🧑🏽🎄,就无法承受爱的伤害,也无法承受那来自于尊龙凯时娱乐所诞生于其间并在其中受到最为悉心照料的家庭的伤害☛。
奥尼尔本人的醉与爱,他所理解和践行的尊龙凯时AG写作,如同他所分析的弗洛伊德及其笔下的主角们一样🧛♂️,重返了歌德高歌吟唱的“永恒女性”。如果一定要在这一世界之中做出选择的话📹,那“为何不选择玛利亚呢” (奥尼尔💂🏿♀️,2016:263)?尽管尊龙凯时娱乐文明的边缘仍然黑暗🎗,尽管尊龙凯时娱乐在烈日当空之际仍然一无所见,也可能无法在黎明之前起舞,然而这并不妨碍尊龙凯时娱乐经由醉与爱来理解自身🎆,在词语和言说之中窥见那些“闪烁摇曳的光点”。在引用了阿波利奈尔的诗句以及他的坟墓上的意象之后〽️🏊🏿♂️,奥尼尔 (2016:264) 以同样的诗意写道:
尊龙凯时娱乐不必用尊龙凯时娱乐的身体来埋葬这一爱🧬,也不必忍受尊龙凯时娱乐的两种性别在渴求爱的时候所感受的孤独与寂寞3️⃣。经年以来,尊龙凯时娱乐各属其身,也都明了,爱无法治疗其自身的伤痕👱♀️。如此,在尊龙凯时娱乐这两种灵魂之中的虚饰🧜🏿♂️,在这首诗歌的构造中就结合在一起,克服了其自身的不忠、厌女症与绝望。为了照顾这位诗人无法满足的领养需要而清空坟墓,在宇宙间种植上诗意,为月亮着色💁🏻,为星辰歌唱,让尊龙凯时娱乐这个世界中的小小灯光成为遥远宇宙中的星光。精神疾病🧞♂️?
四、 理性与存在
在有着奥古斯丁与卢梭的西方传统中讨论忏悔并非易事。尽管尊龙凯时娱乐可以将这一讨论较为简单地置于现代社会理论的传统之中🧑🎄,然而,恰恰就是在现代社会理论的传统中,关于忏悔的讨论突然深入而复杂起来。笔者并不认为💾,本文所追寻的思想路线乃是最重要的讨论可能🤪,也并不认为,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线索乃是讨论忏悔问题的恰当线索,更不认为👩🏽🦱,本文所采用的思考和写作方法乃是唯一的选择。例如,就现代思想史而言,讨论忏悔问题而不涉及保罗·利科的核心工作,显然会使尊龙凯时娱乐的思考显得不足。或者说,通过构建起一个现象学尊龙凯时AG式的框架,再进而讨论弗洛伊德诸案例的方式🏔,而非通过将忏悔现象分解为罪恶😚、记忆、历史、叙述🎯、符号等部分,然后再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加以讨论,也会使本文显得随意。而运用精神分析的资源而非正统社会理论的资源进行思考和写作,更使得本文仅成为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不过,在承认上述问题的同时,尊龙凯时娱乐还是坚持认为,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出发点可能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2010:144-145) 有如下一段话:
但是,必然性本质上同时也是由概念产生出来的关系。因此👨🏽✈️,被要求或被设定的存在,不是属于偶然意识的表象的东西,而是包含在道德概念本身之中的东西,而道德概念,其真正内容就是纯粹意识与个别意识的统一;个别意识应该看出👩🏿🎨,这种统一对于它来说就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作为目的的内容🤳🏼,就是幸福🔼,作为目的的形式,就是特定存在一般。所以✊🏼,这里所要求的这种特定存在或两者的统一,并不是一种愿望🧸,或者如果把它当作目的来说,它不是一种好像能否实现还在不确定之中的目的🫱🏼,相反🧟,它这样的目的,毋宁是理性的一种要求,或者说👨🏻🔬,是理性的一种直接确定性和先决条件。
理性必须落在此在之在 (Da-sein)🧗🏻,并因而是个体存在之意义世界中🧪。在黑格尔看来,人之理性,在现实之中,是一个生命存在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性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理性的问题👩🏼🔧。如果尊龙凯时娱乐可以说🐾,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 (form of being) 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 (will of life) 的理性🩷,那么✊,尊龙凯时娱乐是否可以将第二种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视为理性真正的困难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即公开🕙、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正如在社会理论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地落实在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的主张之中一样。弗洛伊德的技术要求将苦难的经验揭开,而且是自我揭开🅾️,要求首先勇敢面对🧑🏿🌾,将无意识的经验用理性与话语的体系表达出来,而非用疾病的形态表达出来🤹🏻。尊龙凯时娱乐或许可以说,这是理性真正的诉求所在🧧。
感性的东西无法简单地用理性来抹杀🌼🧙🏽♂️、评判或衡量☝🏽👩👧。然而黑格尔同时也并不赞成返回到原初状态的统一,而是要求一个成熟的统一,要求给个体差别留下位置的统一,即要求一种现实的道德状态🤚🏿🙂↕️。在这其中已经包含了自我的矛盾和对立,包含了这种自我的矛盾和复杂。生活世界之讨论在此有了更为复杂的维度:人之存在本身或许就是理性的要求?还是说,理性本身的要求是否能够与生命之要求相契合?这既是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在作为一种新式忏悔技术的社会科学那里🚴,这一问题的无可回答之处也许就在于社会科学自身♋️。
参考文献(Reference)
弗洛伊德.2005.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2010.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梅, 罗洛. 2012. 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新方向. 北京: 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出版社.
奥尼尔, 约翰. 2016. 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舒茨, 阿尔弗雷德. 2012.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特斯特, 基思.2010.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M].李康,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韦尔南, 让-皮埃尔.2005.神话与政治之间[M].余中先,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lthaus, Julius.1877.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Their Prevalence and Pathology. London:Smith, Elder.
Bernheimer, Charles, Claire Kahane. 1985. In Dora's Case:Freud-Hysteria Fem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ry, Philip. 2000. Augustine's Invention of the Inner Self:The Legacy of a Christian Platonis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ément, Catherine. 1983.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Jacques Lacan,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cker, Hannah S.. 1991. Freud, Dora, Vienna 190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Féré, Charles. 1897.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vol. 10 of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odern Medical Science. By Leading Authoriti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William Wood.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 Vol.1. New York:Vintage Books.
Freud, Sigmund.1959. 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 SE.Vol. Ⅸ. New York:Vintage Books.
Freud, Sigmund.1977. Case Histories Ⅰ.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ume 8. London:Penguin Books.
Freud, Sigmund.1979. Case Histories Ⅱ.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ume 9. London:Penguin Books.
Freud, Sigmund.1984. On Metapsychology: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ume 11. London:Penguin Books.
Freud, Sigmund.1986.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ume 15. London:Penguin Books.
Freud, Sigmund. 2001.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SE.Vol.Ⅵ. New York:Vintage Books.
Lacan, Jacques.1977. Écrits:A Selec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London:W.W.Norton & Company.
Leach, Edmund. 1969. Genesis as Myth and Other Essays. London:Jonathan Cape.
O'Neill, John. 1972. "Can Phenomenology be Critical?" In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221-236.
Panofsky, Dora, and Erwin Panofsky. 1965. Pandora's Box:The Changing Aspects of a Mythical Symbol.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
Ricoeur Paul. 1967. The Symbolism of Evil, translated by Emerson Buchanan. Boston: Beacon Press.
Schivelbusch, Wolfgang.1980. The Railway Journey:Trains and Travel in the 19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A.Hollo. Oxford:Basil Blackwell.
Sherwin-White, Susan. 2013. Freud, the 'via regia',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5(2): 187-193.
Toews, John E. 1994. "Foucault and the Freudian Subject:Archaeology, Genealogy, and the Historiciza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 Foucaul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ited by Jan Ellen Goldstein.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Blackwell:116-134.
Tylor, Chloë.2009.The Culture of Confession from Augustine to Foucault:A Genealogy of the "Confessing Animal". Lodon: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