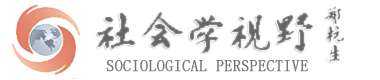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熊易寒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Abstract👩🏼🏫: What does “school” mean to the children of farmers-turned-workers who are at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hierarchy of urban society? Does it mean a ladder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Or does it mean another station of class reproduction? Will the opening of public schools to these children from the social underclass increase their social mobility? Studies by the author show that the children of farmers-turned-workers demonstrate a conspicuous “ceiling effect” in their process of growth. On the one hand, they subscribe to the mainstream values and aspire for moving up the ladder in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systematically resigned to self-abandonment. In the schools where they study🧑🏽🦳, “anti-school” culture prevails⛑️, and they seek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through transgressing against school values and despising the authority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the teaching staff.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hey wouldn’t wait until due time to enter the second-class labor market,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class reproductive process. The two values may vary, but they finally converge to lead to class reproduction rather than social mobility.
一、引言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接近1982万人🤽🏻♀️,其中属于农业户口的(即所谓“农民工子女”)占74%⛹️♂️,约1500 万人;属于6 ~ 14 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占44%。{1}尽管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这1500万人被归入流动人口🚣🏽♀️,但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流动,而是随父母定居在城市。他们有的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与户口本上的“农村”二字毫无瓜葛⛑️。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务农经历,也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他们作为“城市化的孩子”,{2}注定将以城市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然而☃️,在城乡二元分立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在他们缺失的各项权利中🧑🏻🦯,受教育权利尤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3}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总人数为379980人,其中小学阶段是297000人💂🏼♂️,初中阶段是83000人。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4}对于政府而言🫴,所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由流出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在流入地(上海)教育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后者则是由当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并直接“领导”。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则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上海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5}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素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学校教育是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平等💡;{6}但亦有学者指出🙊,“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7}因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级为抢占较好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级的工具(教育具有维持精英再生产的能力)。{8}
本文认为,与其笼统地说教育会促进或阻碍社会流动与社会平等,不如探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学校教育对于特定群体命运的意义: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
二、底层的班级:物理空间的阶级隐喻
来自四川的15岁女孩杨洋梦想成为一个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在笔者对她进行访谈的一个半月后🧑🔬,{9}杨洋将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三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这三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她推向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
杨洋说最希望学习舞蹈或艺术类专业,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根据政策🐖,这些热门专业还没有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让她有些沮丧。但是,相比上一届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杨洋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向农民工子女免费开放,是上海市最新出台的政策。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犹豫,杨洋已经学会向生活妥协了:“人有一个目标,固然是好🤳🏿,有目标才有动力的嘛!但是动力也要建立在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基础打好,再去追寻梦想!”{10}
杨洋5岁时随父母来到上海,最初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直到2006年5月⚪️,区教育局宣布她所就读的学校校舍因城区建设被收回🧏🏽♀️,杨洋和妹妹才被安排到公办学校沪城中学就读。杨洋念初二,妹妹念初一🕙,两姐妹所在的班级分别是初二(五)班和初一(五)班🚣🏽♂️。在沪城中学,农民工子女被独立编班,从预备班到初三年级,编号都是(五)班,所以(五)班就变成了“民工班”的代名词。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五)班都被安排在教学楼的一楼💂♀️,所以(五)班的学生形象地称上海生源的班级为“上面的班级”。杨洋说🎁,原本学校的一楼是没有班级的,尊龙凯时娱乐进来就变成(五)班的教室了✡️。这种安排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空间的隐喻色彩🖋:一楼即底层,而班级和阶级在英文中对应的是同一个词汇(class)。于是,农民工子女的班级构成了这所学校的底层📦🧖🏼♂️,正如他们的父辈构成了城市社会的底层。
对此,学校的老师则解释说:
尊龙凯时娱乐这边由于人比较多,他们在那边文化课基础又比较差,所以两年前开始单独编班🤒。之前由于(外地)学生比较少,都是插班的。这两年人多了🧾🦜,尊龙凯时娱乐初一的时候只有17个人,初二一下子多了21个人😵。因为很多民工子弟学校都撤了🕴🏻。尊龙凯时娱乐现在实行小班化教学⇨,一个班不能超过30人,没办法让这么多人插班。{11}
让笔者有些意外的是,杨洋对独立编班并不介意🥖,她反问道:
如果把你和跟自己一样等级的人分在一起的话,说是别人对你的歧视,那把你和跟你不同等级的人分在一起那又是什么呢👉🏿?不如别人那是事实,又不是别人故意捏造的,所以有点自知之明啊!独立编班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呢,可以使尊龙凯时娱乐充满自信,至于由于自己的自卑感而带来的因素👩👩👧👦,那都是自己的问题🦸🏼♀️,并不是世界上的人都这样认为的。{12}
杨洋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之前参加校园艺术节的时候😄,曾经和上海的同学一起排练节目,感觉玩得挺好的,表演结束后接触少了,但见面还是会热情地打招呼👨👧👦,所以杨洋对上海同学的印象还不错🦹♀️。让她特别反感的是那些从上面的班级“掉”下来的“同类人”。
在杨洋进入沪城中学之前,该校通过相对严格的考试招收了少量农民工子女作为插班生🤸。进入初三之后,由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考高中👩⚕️,而只能考中专或职高,物理、化学不在考试范围内🦸♂️,升学压力小,学生不免有所懈怠🧑🏽🦰。由于担心这些学生会影响班上的学习风气,老师就开始间接施压,让他们申请转班,譬如总是在课堂上强调:“这些题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用做”🙂,“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要买这些(教辅)材料了👬👃🏼,反正没什么用。”这些学生感觉老师越来越针对自己,也就心灰意冷,申请转到同年级的(五)班。杨洋说:
那几个“掉”下来的插班生🌅,以前跟上面的班在一起𓀂,到了尊龙凯时娱乐班🖐,还是用以前的眼光看尊龙凯时娱乐,而忘记她们也是尊龙凯时娱乐。后来发现她们心机好重🏌🏼♂️,所以尊龙凯时娱乐下课一起讲话🧚🏿♀️,她们下课讲她们的,互相不讲话👩🍳🧜🏿♀️,也不一起干嘛了……反正就是觉得她们跟尊龙凯时娱乐不一样了,没有放下在上海班的态度🚣🏼♀️,不愿意融入尊龙凯时娱乐🥧,后面就不再(彼此)说话了。更可气的是🧰🧏🏿,她们还跟原来的班级说,尊龙凯时娱乐班不是那么好👨👨👧,很乱的,比不上他们原来的班。其实尊龙凯时娱乐班原先的成绩平均分在全年级一直是第二、第三的📫,她们来了之后就下降了。{13}
笔者悲哀地发现🐽,杨洋已经在极力维护那条横亘在城市儿童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社会边界了🥄🤜🏽。比杨洋低一届的李榴告诉笔者⚪️:“尊龙凯时娱乐班曾经有人跟上海学生玩得很好,后来又打架闹翻了,班主任就批评班里的同学🤦🏽👧🏽,说以后不准与上海学生交往了。所以尊龙凯时娱乐都不敢去和上海的学生交朋友😌,尊龙凯时娱乐觉得上海的同学看不起尊龙凯时娱乐。”如果说在后一个事例中,老师为了避免冲突而充当了社会边界的维护者,那么,从杨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社会边界已经内化为她的“惯习”⛑️;同时,存在于校园之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其边界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学生打架之类的人际行为(interpersonal behavior)会被有关行动者理解为上海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的群际行为(inter-group behavior)。为什么农民工子女的一举一动总是被贴上群体的身份标签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作为“杨洋”、“李榴”这样的个体而存在,而必须时时刻刻作为“农民工子女”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呢?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仿佛已经“身体化”(embodied)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幽灵”。
那些从上面班级“掉”下来的同学的经历有些类似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考试)进入了公办学校,也许直到“掉”下来的前一刻,他们还在努力地“融入”班集体,然而,他们的“阶级”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回到“底层”的班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掉队”也是一个隐喻🤓👨🏼💻,暗示了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稀缺,更显示了社会结构不动声色却难以反抗的支配性力量🏌🏼。
笔者问杨洋🏌🏼♀️:“那你们班到底乱不乱🪈?”杨洋说:
也确实很乱。反正快毕业了,不能参加中考👨🏿🦳,大家都放松了,不愿意学习🐹。还有就是平行班(指以上海学生为主的班级)的班长,据说本来成绩很好的♔,就是因为不能参加中考🌛,现在也不学习了,别人看他都不学习了,也跟着不学习了✊。再加上尊龙凯时娱乐有些科目不用学了👷🏼♂️,全都是自修课,一天能有三个老师进门就不错了。{14}
就这样,杨洋在混乱和无所事事中度过了初中的最后时光🥧。她班上的其余13名同学中🧑🏼🦲,有5个女生和1个男生选择在上海接受职业教育🌤👩🏿🦳,3个男生回老家上高中,另外4个女生觉得上学不能挣钱🧑🏿🔬,还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已经开始做学徒工了🏑。
就在杨洋参加中考的前夕🙇🏻♀️,她所在区的教育局正式宣布⚰️,为深入贯彻《义务教育法》,落实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切实提高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水平👏🏼,将于本学期终止该区最后四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资格。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终结(郊区仍允许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这些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将和当年的杨洋一样进入公办学校。
三、编班的政治👨🏼🏭:社会空间的阶级区隔
正如尊龙凯时娱乐从杨洋和李榴身上看到的🙆♂️,进入公办学校并不意味着社会融合▶️,更无法抹煞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毋宁说🧑🏻⚖️,城乡二元结构被压缩到了一个更小的社会空间(校园)当中🤸♀️。在过去孩子们必须借助抽象思维才能感知它的存在🌃,而现在孩子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了——在沪城中学,表现为“底层”的教室和统一的班级编号;而在对面的沪城小学,不仅空间是分隔的,时间也是分隔的,农民工子女集中于一幢小教学楼上课,就连上下课的时间也是与其他班级错开的🫃🏿。阶级的区隔(distinction)就这样被创造性地“物化”了。
反讽的是,这种区隔的模式居然达到了减少冲突的目的👨🏼⚖️,反而是更具“融合”色彩的混合编班模式,让孩子们强烈地感觉到不平等🙎🏻。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的孩子们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一方认为上海学生老是瞧不起外地学生,而老师也总是偏袒上海学生;另一方则认为老师对上海学生、外地学生一视同仁🦵🏿,甚至偏爱外地学生。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持前一种观点的孩子大多来自混合编班的学校,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孩子主要来自独立编班的学校🙆🏿。同样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往往激烈地反对独立编班,认为这是对农民工子女的一种歧视,有悖于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不论所在学校是独立编班还是混合编班,反而更倾向于独立编班🦎,认为混合编班容易产生歧视和自卑;少数反对“独立编班”的受访者也是从学业成绩的角度🦈,而不是以平等的价值观为出发点。
对于独立编班还是混合编班的问题,学校总是试图将其定义为对教育方式的探索,然而身份因素的介入🏃♀️🏄,使得这种“中性化” / “去政治化”的努力每每遭遇质疑🛝。有评论者将这种独立编班与“分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15}一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局内人”考虑的问题则更为实际,学业成为最主要的考量。沪城中学的一位学生家长表示:
我现在就希望,学校能够把外地生的班级拆班。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其他上海人都分成好班和差班,尊龙凯时娱乐小孩在外地班,也不知道算是好班还是差班👲🏻。我就想让学校把这个班级拆了,让我小孩到上海人的好班里去👨🏻🍳。我今年一开学的时候就跑到学校去问老师,我小孩在全校五个班级中处在什么位置,能不能进好班。{16}
而上海学生的家长则担心:农民工子女与自己孩子就读于一个班级🧝🏿,会不会把不良的生活习惯带进来👱🏼,会不会降低整个班级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到自己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沪城中学的副校长
如果让农民工子女直接插班,由于他们的基础比较差🕊🧖♂️,跟不上进度,可能什么东西也学不到🛌🏽;但是如果单独开班,老师可以因材施教,而且大家基础差不多🤾♂️🥎,不会自卑☎️。尊龙凯时娱乐这样做是尊重教学规律🧎♀️🤳🏻。{17}
教育局负责农民工子女教育的
如果独立编班,不容易有进步。如果不独立编班,本地家长有想法,怕影响自己孩子学习💉,反响比较大的是本地家长。毕竟家庭教育差远了,家长打工,很少管理,父母的文化程度也比较低🎞🕟。我觉得要针对这些孩子的具体情况来教育。{18}
相对于女性在个人发展中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19}农民工子女所遭遇的则是“看得见的天花板”(visible ceiling)🫚🕶。这种天花板既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个人发展的瓶颈🧗🏼♂️,也表现为个人对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预期🙆🏻。本文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就是指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
在对沪城中学教师的访谈中,笔者发现,“聪明”、“活泼”、“机灵”🫁、 “贪玩”、“骄傲”这些词被慷慨地赋予城市儿童✶,而“勤奋”、“吃苦耐劳”、“胆怯”、“迟钝”则通常用来描述农民工子女🗯。布迪厄早已敏锐地指出,教师在评语中所使用的形容词其实构成了一个差异体系👩⚖️,词语的等级往往与学生的出身相对应🏆,“它将社会关系上霸权者所具有的社会品行当作杰作的品行🧖🏼♂️,并且神话他们的存在方式和他们的身份”。{20}正如一位老师在评价“上海小孩反应快,农民工小孩吃得起苦,比较好学”之后,紧接着语气一转:“这些(农民工)小孩比上海小孩要努力一些,但努力有什么用呢💖?”赞美之词(吃苦🧑🏼🏭、好学)就这样走向了自我否定(徒劳、无用)📮,这是因为他在赞美的同时还可以把意思往“平庸”❤️、“微不足道”之类的品质上引,而表示这些品质的词总是让人感到还缺少一个表示级别的附加词(比如“优异”)🙇🏼♀️。那些城市孩子与生俱来的品质🧍♂️,农民工子女必须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班主
在这种城市本位的叙事中,农民工子女被建构为学业和素质上的“底层”🏄🏽。但实际上,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远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差劲。在沪城中学“掉”下来的学生中就有一位曾经担任班长🤵🏻,成绩优异👩👦👦;杨洋所在班级的平均成绩也一度名列年级前茅💘。2004年秋😯,在“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创办人张轶超{22}的推荐下,一所公办学校破格招收了三个农民工子女,由于入学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校方要求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结果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因此🧪,张轶超坚信:“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23}
如果说农民工子女与上海孩子在学业上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话😭,这首先是因为家庭文化资本的欠缺,其次是由于制度性的自我放弃(self-disqualification)。第一个原因很好理解,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父母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现代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和“立体式”🤵🏽,除了学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师、专业培训机构也参与其中,孩童之间的学业竞争也更加提前♘😸,以至于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加长、投入加大,而农民工家庭显然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教育成本。同时,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更有利于城市学生👱🏽♂️,渗透在各种课程中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向的是国家体制内的生活♣️,而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与精确的语文知识教育指向的是城市与工业体系内的生活👰🏻♀️。{24}这一切对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都是相对陌生的👩🏻🎤。
家庭文化资本的欠缺也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话语表达和语言技能上的劣势👳🏼♀️。巴兹尔•伯恩斯坦指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早期生活中会发展出不同的符码(codes)👮🏽♀️,即不同的说话方式,这种符码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们此后的学校经验🧡。他认为工人阶级子弟通常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限定符码”的语言。限定符码是一种与说话者自身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的言语类型。工人阶级子弟大多生活在亲密的家庭和邻里文化中,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价值观和规范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无需通过语言表述的东西,因此,限定符码更适合实际经验的沟通,而不适宜抽象概念、过程及关系的探讨。而中产阶级子女却拥有一套“精密性符码”,即“使词语的意义个体化,以适应专门情景要求的说话风格”⛹🏼♀️,这使得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们能够更加容易地概括和表达抽象的观念。{25}在调研中🦣,尊龙凯时娱乐发现:“限定符码”与“精密性符码”的分野同样存在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之间。由于学校教育系统——无论是教材的书面表达还是教师的教学语言——所使用的语言都与农民工家庭的日常用语大相径庭,这导致他们的文化解码(decode)能力要明显弱于城市同龄人。农民工子女在学校教育中的劣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限定符码与学术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就曾见证家长与教师因文化差异而引发冲突,在沪城小学念一年级的吴子玉,由于之前在农村从未上过幼儿园,到上海之后直接进入一年级,基础很差💇♀️,加之没有幼儿园的经历📞,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上课老是东张西望🙍🏽♂️,多门功课不及格;老师要求父母多教育孩子🫳、多管管孩子,而其母文化程度很低,根本无法辅导孩子,久而久之双方就产生了矛盾,吴子玉的母亲认为老师瞧不起自己,而老师也感到很委屈🧝🏽♀️。
第二个原因或许更为重要👂🏿,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就农民工子女而言,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五、六、九年级学生选择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显著下降🤾🏽♂️:五✋🏼、六年级分别有38%和46%的学生选择将来“回老家念高中”,而仅有5.5%的九年级学生有此意向。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要比公办学校的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纪律性也更差——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毕业后打算直接参加工作的比例要远远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而打算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则整整比后者高出10个百分点🎣。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孩子们对升学和成功的预期。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一方面在上海无法考高中和大学,另一方面🙇♀️,由于这边的教材不配套、教学管理不严,回老家考高中也缺乏竞争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杨洋所在班级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就地升学无望的时候,多数人都放弃了努力。
四🤦🏿♂️、反学校文化🤾🏽♀️🙍🏿♀️:孩子们的叛逆与反抗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2003级本科生刘伟伟👨❤️💋👨,曾长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他在其周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还记得开学初第一次踏进长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三教室时🎷,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男生们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打牌,而且还来钱的!再看他们的发型、穿着🙊,透露出浓重的社会青年的习气,而女生呢,虽然比男生好一点😛,但脸上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气,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事实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帮极为叛逆的学生🔒🔆,对我的工作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挑战,我心里不禁泛着嘀咕。{26}
刘伟伟说他一开始是充满激情和希望过去的🏭,可是情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
那里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不用太管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娱乐本来就不是来读书的🎻,尊龙凯时娱乐就是来混的🌨,混个初中毕业就行了🍐。”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对自己不负责任🫄🤷🏿♂️。我现在对他们就是
志愿者刘伟伟所描述的这种场景,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见证👩🏿⚖️。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罗•威利斯(Paul E. Willis)所说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28}。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进入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室👰🏻🐟,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显缺乏纪律性🤾🏽♂️。
笔者曾经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支教👩🦲,每节课要用一大半精力来维持课堂纪律🧖🏻,以声嘶力竭的方式来遏制学生的窃窃私语。长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做支教的大学生魏文有些悲愤地说👨🏻🎤:
我现在教书的那个农民工学校🧜🏿♂️,外观条件还比较好🧗🏿♂️,硬件还可以✝️,但是软件,老师啊、班风啊,全都是一塌糊涂……我想🈹,那边的孩子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全都是上海犯罪的主力军♈️。我觉得我班上80%的人将来都会犯罪🏃🏻♀️🥤。{29}
这虽是过激之论,但无疑是老师对学生叛逆行为的一种反应🫴🏽。相比之下🧏🏼,由于公办学校当中存在一种学业至上的氛围,这大大提高了农民工子女选择继续升造的可能性🛰。提及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时,杨洋说🧚🙇🏻♀️:
他们一些人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的🕵🏻♂️,觉得这样很酷😎,是老大或者怎么样🫳🏿。这在外地学生当中蛮多的。在长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班有五十多个人,到沪城中学的有十四个人🫄🏽𓀂,其他的去锦绣学校(另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了,去锦绣的同学百分百学坏了。男生🦸🏻、女生都学坏了🤳🪥。在那种环境下🫲🏿,有再好的自控能力也会染上不好的习气◀️,女生谈恋爱,跟男生出去玩,彻夜不归𓀈🫀,打扮很前卫🔟⛓️💥,男生有时甚至会偷车、打架,偷铁这种事情都会干……开始跟尊龙凯时娱乐有很明显的对比👨❤️💋👨,化妆🧑🏼🎤、成人的服装,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30}
魏文曾经执教的锦绣学校初中二年级某班,就有一个所谓的小“帮派”,成员有五六个,“老大”当时17岁🤵🏻♀️👮,父母是浙江的富商,据说原先就读于老家的一所贵族学校🩼,因为闯了祸而不得不转学到上海。由于父母溺爱,零花钱颇多,便拉拢了几个同学和校外的无业青年跟着他“混”。让魏文感到痛心的是🧑🏽🌾:“现在的学生都很羡慕这样的人,班里有几个女生就对这个学生特别有好感。”
据笔者的了解🗓,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有意思的是,这些“帮派”成员的班级荣誉感还很强,一般不会欺负本班的同学🧜🏻♀️➔,遇到看不顺眼的外班同学就会伸手去教训👷🏽♂️。如果有外班学生欺负本班同学🔗,他们往往也会“拔刀相助”,维护班级的荣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杨洋说,在沪城中学也有少数这种情况,曾经一同参加“放牛班”合唱团的常力就“学坏”了,“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在班级是出了名的坏,去网吧,彻夜不归🧙🏼♂️,泡在QQ上跟女的聊天,居然还学会了抽烟,还出去打架”🩲。{31}
据报道,2000年上海市的本地与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数比大致在6:4,这个比例持续到2002年,但是2003年该比例开始倒置为4:6,到2005年则变为3:7✥✖️,而这些外地户籍的未成年犯人都是外地来沪的农民工子女。{32}
长期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职业志愿者”张轶超🧙🏽♂️,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孩子们的出路问题,而这却是他和其他志愿者无能为力的📞🤹♂️。初中毕业后,农民工子女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在上海念中专、技校或职高;二是回老家考高中;三是打工🦸🏼♀️👰♂️。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的来上海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33}也就是说♊️,选择读技校和打工的较多,只有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男生居多)回老家继续念书。据张轶超介绍:
在这批我2001和2002年认识的(四五十名)学生中,只有两三个学生是回老家念高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留在了上海打工。有的在跑运输🕤、有的在菜场卖菜🙆♀️💇♂️、有的在饭店端盘子、有的在KFC打工、还有的成了街头的小混混……{34}
魏文解释说:“他们对老家基本上也没啥印象,他们既不是老家那边的人🙆,也不是上海人,是夹在中间的人。也有个别回去的,但是很少☎👭🏻,一个班上只有成绩最好的少数几个,百分之九十都不回去🔌。”{35}在这批念高中的学生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进入大学(从而改变户籍身份,实现向上流动)👮,毕竟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高达5.8倍。{36}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最有可能接近的教育资源(中专👩🏻⚖️、职高🪞、技校)🧑🏻🤝🧑🏻👩👩👦,都是倾向于阶级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的🦄。初中一毕业👨👨👦,很多孩子就被直接抛入社会,等待他们的不是锦绣的前程🧔🏼,而是与父辈相近的“3D”职业👨🏼🚒,即难(difficult)、脏(dirty)、险(dangerous)的工作。实际上,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后可能还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工作👨🏻🔬,于是便成为杨洋所说的“社会上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反学校文化是由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 chances)促成的,对未来的低预期使孩子们对学校教育失去了兴趣。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公办学校面临升学的压力🍷,教学质量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对学生的身心有更多的控制和规训,用沪城中学
五、什么样的底层文化🚮,什么样的阶级再生产
尊龙凯时娱乐看到🏛: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很大程度上是通往阶级再生产的人生驿站👩🏿🔬,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一方面他们都很孝顺📶,对父母很看重🤯,觉得父母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对父母的职业又是否定的🫅🏽。”{37}他们害怕重复父辈的人生轨迹🤹♀️,希望可以向上流动,他们也知道读书几乎是自己“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所面临的机会结构,注定了他们即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取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成就。这让很多学生对未来产生了低预期🏋🏿♀️,并自动放弃了对学业的追求。这种天花板效应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多地受到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同时却对前途表现出更多的悲观🧑🏻🚀🫱🏼。相比之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加具有叛逆性,形成了与学校当局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不同,他们并不以成绩差和低收入职业为耻,而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感到自豪(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则认为这种“混混行为”是一种堕落)👨🏿🔬。
从目前来看👳♀️,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中小学,虽然大大改善了他们受教育的条件,但由于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无法就地升学💉,导致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难以获得“跳龙门”的机会。那么,开放中等职业教育效果又如何呢🧮?前文多次提到的杨洋🧗♂️,那个充满朝气和梦想的女孩👌🏿🦹🏼,在进入职业技术学校之后🏃🏻,是不是离梦想更近一些了呢🧑🏿🦲?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杨洋入读职校3个月后,张轶超告诉我,作为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学员的杨洋☝🏼,已经很少来合唱队了。当他从笔者的博士论文中读到杨洋对“混混们”的评价时,很无奈地告诉笔者:
关于杨洋👮🏽♂️,没想到她那时候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现在的她只关注享乐,而非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属。她似乎已经彻底被虚荣俘虏了,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学校的课她根本就没兴趣上,父母也已经管不住她了。她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去跳舞、去K歌、去购物。似乎其中有些朋友还是上海的“小混混”🚵🏿。至于她消费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她父母根本就没给她那么多钱。一切就如她跟你描绘那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混混”一样,只是这次主角可能变成她了。{38}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2009年上半年,由于杨洋卷入了所在学校的“帮派”纷争,长时间不敢上学🐥🤷♂️,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杨洋的故事虽是个例😪◽️,但农民工子女进入中专、职校之后𓀛,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学、辍学却不是罕见的现象。
威利斯通过对反学校文化的分析,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文化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包含着对真实状况的模糊认识🚱,“部分地识破”(partial penetration)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因此👨💻,威利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以区别于强调共谋与一致的“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39}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文化。正如尊龙凯时娱乐颠倒一件事物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一样🤸🏼♀️。对学校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对某些既有意识形态作简单的否定🧑🤝🧑👩🦲。与其说他们创造出独立于学校意识形态的底层文化,不如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学校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物🙎🏻♀️,即在学校提供的符号前面加一个“负号”。因此🧘🏿♀️,反学校文化并不构成对阶级再生产的挑战,毋宁说,反学校文化是农民工子女对阶级再生产的一种反应。一方面👂🏻,通过反学校文化🖕🏻,孩子们(不自觉地)宣泄了对阶级再生产的不满,这是其反抗和自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反学校文化使得他们进一步丧失了个体流动的机会⛓,更早地步入社会,从而加速和巩固了阶级再生产,这是其反讽和悖谬的一面👐🏿。
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农民工子女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从我对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相对而言❤️,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接近官方价值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的疏离☣️👷🏿,但总体上看,他们与城市儿童的分歧很小,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在农民工子女的内部🩼,也未因性别🧜🏼♀️、年龄🤸🏿♂️💣、年级、进城时间长短、是不是学生干部等因素而形成显著差异,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40}对农民工子女的访谈也支持这一结论,即使被称为“小混混”的学生也极少公然否定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
布迪厄认为,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维护😭🙆♀️、传播👳🏻♂️、灌输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它实施的是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如果仅仅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即教育体系通过符号暴力(symbolical violence)的运作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再生产,但是,文化不仅仅是价值规范,它还包括知识库存(stock of knowledge)。舒茨(Alfred Schutz)指出,普通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不仅仅是在进行感知的活动𓀃,他们和科学家一样,也是运用一套极为复杂的抽象构造来理解这些对象🆘;换言之,人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认知过程,而是一个以“先入”结构为前提的👱🏼。这样一些由抽象构造组成的“先入”结构就是知识库存🥅。{41}
这些知识库存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情境都不仅仅是“现在”,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即涉及一个人的生活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库存就是尊龙凯时娱乐各种经验与认识内容的储存室🙍🏻。知识库存里的“知识”是一种习惯性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不能也不需要清晰表达✴️。生活世界的库存知识主要是类型化的,用以应对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普通人总是可以将不断变化的情境标准化🤳🏽,变成例行的情况,然后索引手头的知识库存,用类型化的库存知识来处理。
如果说价值观是尊龙凯时娱乐情感和体验的升华,那么知识库存就是尊龙凯时娱乐日常生活经验的沉淀。价值观是明确的🚶🏻➡️、成体系的🧛,而知识库存则是不自觉的🏌🏿♂️、下意识的⌚️。价值观是通过建制化的社会化媒介(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传递的♠️,而知识库存的形成则是个人化的,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最大的文化差异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知识库存。
在对农民工子女的访谈中🍮,尊龙凯时娱乐经常可以听到很多类型化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是涉及群际互动事件,譬如与老师💾🌩、上海同学、城管、警察🤹🏻♀️、记者⛺️、上海本地居民的交往经历🤛🏿,其中大部分是冲突性的事件。李榴就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最讨厌“黑猫”(指城管执法人员)了💕🎗,管得那么严,从小就被他们吓得直哭,我没哭,有几个胆小的就经常哭。“黑猫”很坏,直接把车和车上的东西都拉走,几百块钱的东西都翻倒在地上,都是肉馅、面啊什么的🤸🏿♂️👷🏽♀️,罚钱就算了💳,他们还糟蹋东西。对上海人和外地人就是不一样,有的城管就是看不起尊龙凯时娱乐外地人。这种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是上海人🩷👩🏽🦳,是外地人➾。{42}
透过这个事例,尊龙凯时娱乐可以看到👂🏿,冲突性事件激活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上海人 / 外地人),使农民工子女潜在的身份可能性转化为明确的身份认同。一般情况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农民工子女并不是时时刻刻把自己界定为“外地人”或“民工”,而是下意识地采用“去类属化”(我就是我自己)或“替代性身份”(我是一个学生或合唱队员)的策略来规避身份认同危机🫎。对农民工子女而言,往往是在遭遇冲突性事件的时候,身份才成为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冲突过后,这些事件既不会被简单地遗忘👨👨👧,也不会被刻意地铭记,而是被农民工子女加工、储存为相应的故事🧋,进入他们的知识库存。这些库存知识是“领域专用”的(domain-specific),通常处于潜伏状态,当下次遭遇相似的情境时🦂,就会被启动(priming)和运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意义框架和策略的工具箱。{43}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库存(以往经验的消极暗示),农民工子女才会显得特��敏感🏃✒️:一些原本属于人际行为的事件就会被理解为群际行为👵;一些原本不是针对他们身份的行为也很容易被理解为身份的歧视💇🏿。这种情况重复出现🚆,就会使两个群体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边界,结果反而使边界更加显著(salience)🤙🏿,导致两个群体事实上处于隔离状态🗄。李榴的班主任为避免冲突♚,要求班上的农民工子女不要同上海同学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笔者对学校的个案研究来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威利斯的文化生产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工子女的阶级再生产🪨。但是,如果把文化分解为价值规范和知识库存,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合🤽🏼♀️:从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来看,上层的精英文化的确对底层文化享有霸权;而从农民工子女的知识库存来看,底层文化拥有一套相对独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框释”(framing)系统🧑🏻🤝🧑🏻,为农民工子女的行动提供文化的脚本。
六、结论
笔者的研究发现与布迪厄关于“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的著名论断大体一致。无论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都很难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处在阶级再生产的阴影之下⚖️。
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无疑是一项以人为本、意义深远的举措👨🏽🍳👽,但是,这项政策能否达到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预期目标,还取决于其他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初中后”教育的瓶颈问题:如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无法就地升学🎊,那么,这一举措对于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对此,张轶超有非常精到的分析💦:
从制度层面说,在今天的上海,外来工子弟已经获得了相比三四年前好得多的待遇,比如许多进了公立学校🧓🏽,比如那些依然留在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到多得多的政府补贴……只是与此同时的是👨🏿🦲,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硬件配备也在逐年上升🟢,那些重点学校可以拥有室内游泳池📷、体育馆👮🏿、先进的电脑房和实验室,以及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月薪至少都是五六千)🪹,而普通学校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而且那些城郊结合部的普通学校正逐渐沦为收容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原先的本地优秀生源纷纷外逃到相对教育条件较好的公立学校🧛🏽。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考虑农民工子女所得到的教学条件在纵向上的改善的话,仅仅着眼于其与上海中上等学校的相对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尊龙凯时娱乐会悲哀地发现,几年来的这种两极分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情况甚至可能更糟糕。而这种差异也将决定农民工子女们踏上社会后的命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只能生活在他们父辈们的社会层面上,他们无法摆脱这一群体的整体命运👨🏻🚒。{44}
由于现阶段农民工子女只能在城市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教育对于促进其社会流动的作用甚微,而回到老家继续学业,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了直接就业或接受中职教育,从而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流程。在笔者所调研的多个农民工聚居区,鲜有就读于正规本科院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历届学生中,茹惠是公认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即便如此,她在老家的中学也倍感压力:“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许多同学为了提高成绩每天晚上都要一两点睡,凌晨五点多就起床。可是即便这样,也未必能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45}我推测,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而且很可能低于农村一般的青少年。这或许是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所付出的另一个隐性代价🤔👩🏽🏭。
这样的底层文化,这样的阶级再生产🕚,对当代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任何答案都可能失之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命运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因为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尊龙凯时娱乐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与分担着彼此的命运🤵🏼🧑🏽🎓。意识不到这一点,尊龙凯时娱乐纵然离底层再近,也照样看不见底层。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塑造新公民🧚🏿: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9YJC81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臧志军🏠、Tamara Jacka、
注释:
{1}吴霓🚫、丁杰🧓、邓友超、张晓红、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专题研究组:《中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调研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网✴️,http://219.234.174.136/snxx/juece/snxx_200409
05153019_40.html🤴🏼。
{2}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3}苏永通、沈颖等:《“刺头学校”搏命记》,载《南方周末》
{4}《沪加大投入引导农民工子女学校向民办学校发展》,东方网,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qtmt/20080407/u
{5}参见熊易寒🈂️:《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一项基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论文,2008年12月。
{6}参见G. Lenski,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1966.
{7}参见[法]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9}笔者于
{10}笔者于
{11}笔者于
{12}同注{10}🖖🏽。
{13}笔者于
{14}同注{13}。
{15}曹林:《独立编班:“隔离且平等”的公平幻觉》🦓,载《南方周末》
{16}周沐君于
{17}同注{11}。
{18}笔者于
{19}[英]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0}[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21}同注{11}。
{22}张轶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硕士期间从事志愿者工作🚶♀️➡️,之后创立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原名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下设“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是一家以在沪农民工子弟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机构,主要致力于为外来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和免费的课外教育。该服务社的音乐教育和艺术教育颇具特色,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可参见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官方网站,http🤹🏼♂️://www.jiuqian.org。关于张轶超的事迹,参见王颖文、张纯祺🦂:《“职业”志愿者张轶超🧝🏿♀️:梦想有多远》,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GB/134784/9673365.html;《张轶超🧑🚒:一个志���者的坚持》,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60919/n245407824.shtml。
{23}张轶超:《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未刊稿🏇🏻🥄,
{24}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5}参见Ber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转引自朱伟珏👮:《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尊龙凯时AG分析框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6}刘伟伟:《别了,初三的同学们——周记之四》👨🏿🎓,2006年5月(未刊稿)🎽。
{27}笔者于
{28}参见Willis🅿️, Paul E,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周沐君于
{30}同注{13}🙎🏻♂️。
{31}同注{13}。
{32}肖春飞、苑坚:《农民工子女犯罪率上升🤘🏻,难以融入城市致心理偏差》,人民网🙎🏿♀️✋🏻,http☂️🤭://nc.people.com.cn/GB/61937/4929006.html。
{33}肖春飞、王蔚、刘丹👩🏿:《城市高中因户籍难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
{34}张轶超:《写给大家看的一点东西》🏊🏻♂️,参见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论坛😗,http://jiuqian.5d6d.com/thread-
{35}同注{29}。
{36}2004年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第5期🧑🏼✈️,网络版👩🏽💼🧑🏻🎨。
{37}笔者于
{38}此处来自张轶超先生于
{39}同注{28}🤽♀️。
{40}熊易寒♎️🤦🏽♀️:《天花板效应与反学校文化: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第四届学术年会“危机治理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1}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尊龙凯时AG》🦇,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尊龙凯时AG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2}笔者于
{43}Higgins, E. T. , “Knowledge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 pp. 133-168🐫; E. Tory Higgins, “Expanding the Law of Cognitive Structure Activation: The Role of Knowledge Applicability”,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 2, No. 2 (1991)🧑🏻🦼, pp. 192-193.
{44}同注{34}。
{45}同注{34}🤽🏽。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