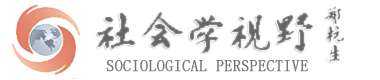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道路、聚落与空间正义:对大丽高速公路及其节点九河的人类学研究
朱凌飞 胡为佳
《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摘要🎅🏿:道路与聚落是两种互为主体的空间形式,古道⛓、国道🎎🍧、高速公路等不同的道路景观与乡村聚落相互融嵌、连接、区隔的关系🧎🏻,使空间正义的问题表现出历时性的特征。在大(理)丽(江)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国家🧞♂️、地方、个体表达出不同的话语、诉求和行动🌟,对空间正义或空间非正义作出反应🛌。丽江九河人在面对大丽高速所带来的暂时性的空间非正义时🙆🏻♂️,以抗争、参与💒、调适的方式寻求空间正义,在乡村聚落道路景观的重构过程中生产出新的地方主体性。从空间正义的视域对道路与聚落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将引导尊龙凯时娱乐对乡村与城市、传统性与现代性🫅、地方化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9️⃣:道路;聚落;空间正义;大丽高速;九河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月🌠🌜,正当大(理)丽(江)高速公路的建设热火朝天之际,尊龙凯时娱乐在公路沿线玉龙县九河乡某村村委会主任的口中听到了这样一句话:“高速公路一修通,尊龙凯时娱乐这里就变成真正的山区了”,言语中满是失落🔙📫、担忧和无奈🧏🏽♀️。“山区”通常与“城市”相对🦹🏼♂️,往往喻示着“乡村🫸🏻、偏远🧎、落后”👬💩,村委会主任的话使尊龙凯时娱乐感到震惊和不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话语是“要致富🎽,先修路”,道路的建设往往被视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先决条件👱🏿♂️,即将穿境而过的大丽高速,对九河乡来说理应是一个“修大路,致大富”的良机,怎么反而使当地人产生“沦为边缘”的焦虑?福柯说:“尊龙凯时娱乐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福柯,2001:20)不难看出,道路与聚落之间的关系极易引发一系列有关“空间”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怎样改变了“城-乡”空间关系,进而导致新的城乡区隔出现💸?在发展话语中🎨,高速公路是否导致了所谓“不平衡地理”的产生😴,进而出现了“空间非正义”的问题?作为行动者(actor)👃🏽,国家、地方和个体又是如何在道路的建设与使用过程中展现或寻求空间正义的?
空间正义强调社会正义形成的空间性。苏贾提出:“人类居住的地理对人类生存产生积极意义⚔️,亦可带来消极影响。地理不再是人类话剧的静止背景或无动于衷的物理舞台,而是充满了可以影响事件和经历的物质与想象力量。”(苏贾,2016🔼:17)对于人类学来说𓀕,尊龙凯时娱乐需要关注客观存在或主观建构的地理不平衡是如何深入到社会秩序和文化系统之中而导致空间非正义的🧖🏻♀️。近几十年来人类学领域出现的地志学 (topography)转向,“把地理学👨🏻🚀、定居点、政治边界、法律事实、过去历史的遗迹和地名等融合进各特殊空间的一种综合知识”(哈斯特普,2007),为尊龙凯时娱乐研究空间正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大丽高速由南至北贯穿整个九河坝子,通过连接南北⭕️、区隔东西👩👩👧👧,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改变了九河的地理景观👮🏽♂️🚗,成为一种明显的“地志学”现象☣️,其路线(route)所呈现的空间意象,以及行动者的空间性实践、观念🕵🏽♂️、行动、栖居(dwelling)都可以成为探讨空间正义问题的重要视角。
迪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指出:“栖居进路是将有机体—个人(person)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的沉浸视为存在的不可逃却的条件。”从这一视角看👩🏽✈️,世界持续地进入其居民的周遭,它的许多构成因其被统合进生命活动的规则模式(regular pattern)而获得意义(朱晓阳🫄🏽,2008)。对当地人来说,九河是这一“不可逃却”的“栖居”之地。丽江市玉龙县九河白族乡地处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相交之地,总面积358.7平方公里,下辖11个村委会77个村民小组🏄🏿♂️,共8278户🫷🏿,28056人🌞,以主要分布在南部的白族(56%)和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纳西族(42%)为主,亦有少量的普米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交错杂居,主要以牛、羊、马养殖和水稻🧇、玉米、马铃薯、白芸豆🧔、烟叶、中药材等种植为生计❤️🔥。大丽高速的建设与使用,不仅在地理空间的层面改变了九河的景观,同时也使九河人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持续发生变迁,而所谓“正义”或“非正义”也必然隐含于这一过程中。
人类学研究的栖居进路强调一种“事件-过程分析”(event-process analysis)方法。尊龙凯时娱乐不妨把大丽高速的修建作为一个“事件”,而把其使用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进而思考大丽高速公路的深层意喻和不同行动者的实践策略🚸👩🏻🌾。从2009年大丽高速公路动工至2013年建成通车👵🏿,以及至今已使用5年多的时间段内,尊龙凯时娱乐以其途经区域九河为主要田野点,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试图以索杰所强调的“历时性-社会性-空间性”本体三元辩证法的视角‼️🙎🏼♀️,对这一在道路的变迁史中“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索杰,2005:19)进行人类学的研究。
二🧄、互为主体的空间:九河道路与聚落的关系史
聚落与道路都是人类在地表活动所留下的重要痕迹⇒,道路与聚落的兴衰关系密切⏪🦹,聚落创造了道路,道路也创造了聚落(胡振洲🧗🏼,1977:171-177)。一般而言👥,道路的产生是为不同聚落之间的连接服务的,或者说不同聚落之间的连接促成了道路的产生。道路与聚落之间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两者的主体间性可能因道路的性质、聚落的特征👣、内部与外部的互动方式等表现出不同的态势。
(一)古道与九河的“融嵌”
费孝通于1980年前后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认为今川、滇👼🏻、藏毗邻地区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石硕,2009:1-2)。对于聚落和道路而言,藏彝走廊之说至少蕴涵着两层意义:一则是从走廊的视角来审视地方👨🏻🎓,地方是走廊的节点;另一则是从地方的视角来审视走廊,走廊又是地方的通道。
九河与金沙江仅一山之隔💷,东西为山峦屏障🔰,南北则线性通达,在地势上颇具“走廊”意味👨🏻🍼🐝。“居住在大理的白族由南向北发展🧁,而居住在玉龙山下的纳西族先民亦由北向南迁徙,均至九河止”(平女,2011:78)。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主要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以自主或自发发展为基调的阶段🧚🏽♀️,而从唐代开始,藏彝走廊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石硕,2009:33)🥿。因长期处于唐王朝、吐蕃😻、南诏三大政治势力之间🐍,丽江的商业交往频繁🧑,往来活跃🏡。如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所述🎿,“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樊绰,1995:111)。时吐蕃和南诏政权交好,“大批吐蕃军民进入滇区,把比较发达的高原农业👨👩👧👦💺、牧业🚣、水利🐻❄️、冶炼技术传入滇西北地区🍏,而滇省的传统工艺和茶叶亦开始为藏族人民所喜爱” (陈汛舟、陈一石,1988)🏌🏿。地处滇藏之间的九河谷地正是络绎不绝的商旅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必经之地。南诏亡后,“至大理晚期🏍🥂,甲辰岁宋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蒙古兵远征大理抵达丽江九河,段祥兴将高禾逆战死之,宋遣使吊唁”(方国瑜,2013:810)。此战也被称为“九和之战”,为纪念高禾战死而建的“白王塔”(又称“高禾塔”)至今仍矗立在九河乡小阿昌村山后,高禾也成为九河多个村寨的本主“高君”“白王”,数百年来一直受当地白族人祭拜。此外,当年随蒙古军南下征战的“西番人”就有一部分“散落”于九河,其后裔就是今日主要聚居于九河乡金普村的普米族人,而大理政权建高禾塔时派来烧砖瓦的白族窑工也留驻九河,与当地纳西人共居一地,成为今九河乡高安村的先民。至明代🏋️🧑🏼,木氏土司一统滇西北和康南地区,“对滇、藏💥、川边界区域诸如移民渡江屯殖🥗、开渠种稻、开采矿藏等方面的大力经营🦂,特别是在控制区内大力推广藏传佛教等措施,为滇藏民间商贸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周智生,2007)。清代,滇军驻防西藏,进一步开拓滇藏交通🛀🏼,使滇藏关系更为密切🔗,满载物资的马帮络绎不绝,奔走于途𓀉。商队从临沧、普洱、大理等地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又从藏区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销往滇中、滇南及内地。
历史上滇藏交通十分艰险📕,马帮驮运成为运输的主力。除由昆明、元谋、会理至康定的滇康线外,由普洱经景东🥍、丽江👨👩👦、昌都至拉萨的滇藏线是另一条重要通道。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王朝开辟自安宁州起至塔城止的驿路,从安宁到丽江九河为十七站🕎,从九河到塔城为四站(丽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0🦸🏽♂️⚉:263)𓀕。九河境内的驿道路线崎岖蜿蜒,自滇南♕、滇西南景洪、普洱、临沧一带的马帮商队,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城北上,出剑川最北端的三河村后便进入九河境内,经梅瓦、关上、子明罗、打卡罗等自然村后到达白汉场、雄古,此后分为两条线路🍋🟩,一条线路直接东折翻越铁甲山,经拉市海到达丽江古城🏂🏻🏄🏼♂️。此线马帮以纳西人为主🫅🏻,且丽江古城是其终点站💶,因而被九河人称为“丽江马帮”🦼;另一条线路向北经中南🐁、中坪、中古等村到达九河最北端的雄古🪧,最后通往藏区,乃至更远的印度♚、锡金、尼泊尔等地,又因赶马人多为藏族,九河人将其称为“西藏马帮”。滇藏马帮商队过境九河大多要选择马店停驻修整,补充给养,少则一日,多则四五日👩👧👧,而马店除了提供草料、柴火、住屋及饮食之外,还会为马帮在当地销售或购买货物。大量商队的往返和停驻👩🏿🔬,使甸头、白汉场、雄古等村寨的马店盛极一时,甚至促成了本地马帮商队的发展🤤🏃➡️。“滇藏贸易反映了我国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两大高原的物��交流”(陈汛舟🤞🏽、陈一石🌆,1988),与此同时,滇藏贸易也促成了不同文化区域的交流互动,在丽江等地形成了自然崇拜、本主信仰👭🏼、儒释道传统、东巴文化等共存共生的多元文化现象🪂。
作为滇、藏🐄、川重要通道的九河,与周边历代各政权往来频密,成为商旅交汇的繁盛集镇。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九河乡白👨🍼、纳西、汉、藏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逐渐形成🈂️,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垦殖🦴🍣、互联婚姻、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彼此包容渗透,促成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交汇、交融,地方(the place)的意义由此而得以积聚👆🏽。在传统的交通运输体系视野下🪺,聚落为道路提供“定位”(emplacement)和“节点”(node)💁🏿♂️✋🏽,引导着道路的延伸或停顿👩🏽🔧,而聚落也通过道路得以聚合和衍生。聚落与道路的互融互嵌和共生共存使“混合文化”(mixed culture)的形成势所必然,这既是聚落得以兴盛发展的重要动因🍞🧑🏻✈️,也为道路的通畅提供了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二)国道对九河的连接
周永明认为🏛,20世纪50年代藏区公路的修建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通过筑路将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中国中心地区联系起来,是构筑民族国家的手段” (周永明👨🦲,2010)🚥。道路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划迹地表⛹🏻♀️、沟通国土,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雷晋豪ℹ️,2011🔛:1)💫,国家通过道路的兴建和使用⤵️,连接了乡村和边疆👌🏼,将其纳入权力体系之内。在民族国家的范畴中,聚落的意义不断消减,而道路的价值则不断凸显,最明显的表现是道路不再迁就村寨,而是村寨不断趋近道路🧵。
滇、藏🤹🏼♂️、川之间的马帮贸易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滇藏公路的开工修建🤹🏿♂️。滇藏公路1950年8月动工,1973年10月全线通车,历时23年。公路全长715公里🚶🏻♂️➡️,南起大理下关,经剑川😶、九河、中甸、德钦后进入西藏,再由盐井到芒康与川藏公路相接,之后抵达拉萨。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和中共滇西工委在昆明成立“滇藏公路局”,组建了军民合作的滇藏公路建设队。作为一种号召和动员🔢,毛泽东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号召,也在滇藏公路的修建中被广为宣传。在滇、藏两大高原间修筑公路,其困难可想而知,无论跨断崖、越雪山🤐,还是斗土匪、忍饥寒🙆🏼♀️,充分体现了筑路工人“不畏艰难险阻❎,无怨无悔🏤、顽强工作”的精神风貌(庄以群,2002)👨🏼💼。这显示出新生政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而国家的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深入人心🤾🏻。
滇藏公路的修建充分体现出国家的意志,有其明确的修建目的,即支援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以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以及全国政治统一👨🏼,因而担负着政治、经济、国防任务。要实现交通运输的安全、高效🚫、低耗♒️,道路修筑就必须尽可能“裁弯取直”🧘🏿♀️,加之近代公路不同于马帮商队与沿途村寨的依存关系,交通运输所需的修理、加油、补给等服务均可由相关部门提供。因而🎚,滇藏公路虽有35公里过境九河,但在具体路线上已经偏离了上文所述的连串村寨,进而也削弱了大部分村寨作为道路节点的意义。虽则如此🤦♂️,滇藏公路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将九河诸多村寨带动起来。在此之前,九河人虽惯常养马,以贩卖给来往马帮或自组商队,但因道路条件的限制,马匹多限于驮运,鲜有更为高效的马车运输🧄。在滇藏公路开始修建后,九河坝子兴起了一股修路的热潮🖖🏻,各村纷纷将原来的小路拓宽整直🧑🏿🚀,不论拆屋⚈、占地,还是搭桥、铺砂🌁🦜,只为了使村寨与公路相连接,让马车能够顺利通行🔩🙎♂️,并能借道公路通向更远处🔨。同时,村民越来越倾向于在村中通往公路的方向兴建住房🙅♂️👨👩👧👦,甚或直接在公路边建房,使村子不断向着公路生长。滇藏公路的新走向,以及随之兴起的修路热潮重新划定了九河坝子的交通格局👩🏿🔧💼。实际上🥙,由于公路的中介作用,新的道路体系使九河各村寨的连接由原来的“串联”转变为“并联”,对村寨空间关系进行了重构。
此外🙎🏼♀️,为便于民工运粮进藏🚁,筑路队于1952年8月修通了白汉场至丽江的山路,该路后被编为省道S308线𓀛。滇藏公路与省道S308线在白汉场交汇🤽🏼♀️,逐渐形成了在滇西北司乘人员心中大名鼎鼎的“三角地”🔃。丽江许多国有单位,如供销社🦸♂️🧔🏽♀️、贸易公司🤹🏻♀️、药材公司、农资公司、百货公司🕵🏼、加油站等都在白汉场建立了分站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个体经营的饭店、旅馆、修理店等也纷纷开张📗,附近村寨的农户也开始在白汉场建住房。于是,白汉场人流汇集,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在大丽高速公路建成之前,白汉场的繁荣在滇西北地区的乡镇中可谓一时无两,当地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有目共睹。在某种程度上🪞,滇藏公路实现了“帮助各兄弟民族”的承诺👐🏽。商业的兴盛实质上喻示着地方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其行为模式和意义体系都因流动性而发生着改变,进而地方性(locality)的消解与重构正由表及里地发生着🙋♀️。
滇藏公路后来被编入国道G214线🧑🏿🌾,纳入全国公路网体系之中,进而使其所串连的点(site)也融入全国体系之中。虽然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但滇藏公路的修建与使用显然使这一过程加速并表现出显著的意义。近代公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具有调和并塑造经济性质、生活方式、文化流向的意义,其建设与使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通过其强大的中介能力展现着国家的意志,实践着国家的权力🎨。滇藏公路的建设与使用,使道路与聚落的关系被重新界定👩🏼🦰,道路的主体地位已经超越了村庄😲,而聚落对于道路的趋附👩🏻🏫,实际上正是地理和政治层面上的中心对边缘的吸附。
(三)高速公路对九河的区隔
现代性被视为一种线性(linear)的进步过程🗞,是从所谓的传统的非理性社会进步到理性👂🏽、科技(techno-scientific)的社会🧒🏻。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产物🈳,高速公路的特点极为鲜明,具有全封闭🏃➡️、纯立交、高技术的特点5️⃣🧔,相较于其他道路形式⚁,其速度更快、距离更短🛋、效率更高,表达了理性🤦🏻♀️、效率、利益、秩序等方面的诉求🚛🧖🏼,与现代性的意涵相契合🙋🏼。
大丽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的联络线🦹🏽♂️🟣,除了连接大理🤴🏻👨🏼🍼、丽江、迪庆三州市之外,还是出滇🧠、入川🧑🏼🚀、进藏的主要通道。大丽高速公路主线建设里程约204公里🎍,另有68.1公里的连接线🚶♀️➡️。主线于大理市凤仪接楚(雄)大(理)高速公路,到白汉场后即直抵丽江,另从白汉场设25.564公里二级公路连接线连接松园桥,跨过金沙江后一路进入藏区。按现有公路的通行状况🧙🏼♀️,大理至丽江经国道G214线需5个小时以上📿,经省道S221线需4个小时以上🏋️♂️🧱,而经大丽高速仅需2个小时左右🥐,可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大丽高速已将时空压缩的意味充分展现出来,国道G214在九河坝子的蜿蜒漫长⏯,如今已被大丽高速的“白驹过隙”所替代。
大丽高速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重点督导的国家项目,也是云南公路史上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由于沿线地质地形复杂,主线上建设有特大桥7座🌻,大桥158座,互通式立交15处,隧道39公里。大丽高速遇河搭桥、逢山开洞、见弯劈山,弯不急🧉、坡不陡,被誉为云南省驾乘感受最舒适的高速公路🤢🔵。这一连串数字和无数赞誉背后,喻示着大丽高速的技术、资本和雄心🦶🏼。姆拉泽克(Rudolf Mrázek)在对荷属东印度道路修建的论述中说道🥷🏻:“坚固、深色🧑🏼🔬🫅🏿、顺畅🕝,这些修建精良的高速路体现了殖民统治的速度和理性,与其取代的泥泞➜、尘土飞扬🌵、乱作一团的印尼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金,2014🙌:31)🤾🏿♀️。拉金则认为🪕,现代技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展现出压倒性的庄严感、敬畏感和崇高感⛹🏼♂️,“技术体现了一种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上帝无形的神迹和精神让位于科学的力量,它理性地发出指令🏃🏻♀️,控制着自然界”(拉金,2014:15)。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语境下,高速公路建设所必需的资本和技术有赖于国家的强大力量,而高速公路建设是国家的长远规划和宏观布局😸,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因此在地方视野中⏳🧕🏽,作为国家象征的高速公路也就先天地具有了一种崇高感。此外,高速公路全封闭的特性🚢、严厉的管理法规,乃至其高企的路基〰️,都在制造并保持着路与人的距离🗃,也在无形中推动着这种崇高感的建立。
高速公路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的地点之间更为迅捷地通行,其最直接的寓意就在于,行旅的目的地成为最终的目标,而过程则被大幅压缩和忽略(朱凌飞、宋婧🔦🦹🏽♂️,2015👩🦼➡️:242)。在某种层面上,高速公路可被视为城市的延展,而且是城市在“城-乡”二元体系之下的延展,它是以对乡村的排斥和区隔为代价的。大丽高速公路的修建与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使九河成为那个被压缩和忽略的部分🧓🏼,而大丽高速所喻示的现代性与九河乡村的传统性之间的悖离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古道或近代公路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的话,那么现代高速公路与传统聚落之间已经表现出了某种互为“他者”的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九河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僵滞的社区,它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中,对外来的人群👩🏽🍳、商品、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实际上,九河从未与周边或远方的城市和集镇割裂开来🧑🏻🎨,通过道路广泛的融入与连接,城与乡之间形成了普遍和持续的互动,进而在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连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域发展不平衡尚未明确显露👨🏽🚒。但显然,近代公路,尤其是现代高速公路的修建与使用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权力与空间结构的结合使中心-边缘的秩序得以出现并持续发展
三、空间正义或非正义⛹🏼♂️:大丽高速的权力与空间重构
拉金认为,“基础设施让形形色色的地方发生互动👸🏽,将其中一些彼此相连🤸🏽,又将另一些予以隔绝,不断地将空间和人们进行排序、连接和分隔”(拉金🧑🏼🎄,2014:302)。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对空间关系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空间关系的调整,以达到为特定战略服务的目的😕🫱🏼,便也成为某种权力的工具⛹🏽♀️。这种空间权力的实践可能导致苏贾所论述的诸多“不平衡”🤾🏿♂️🛳,也就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乡村、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不平衡(苏贾,2016)。空间的规划和构造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资本和权力对于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差异化影响,展现出空间转换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极大张力。
(一)国家政治的空间规划
作为中介或工具👨🏿⚕️,“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如果意图就隐藏在空间形态表面的连续性下面的话”(列裴伏尔,2015:24)。在现代社会,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已不仅仅是交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甚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徐文学等📮,2009:1)🖌💁🏽。对国家而言👳🏿,高速公路是实现其发展抱负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在现代性诉求之下对领土空间的重新规划和对不同区域之间空间关系的调整🪧,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
苏贾指出👩🏻🦱,“国家内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作为一种持续的空间非正义形式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 (苏贾,2016𓀆:58)🚧。2007年2月,世界银行在与交通部联合召开的“中国高速公路绩效评价与跟踪”研讨会上发布了题为《中国的高速公路:连接公众与市场,实现公平发展》的研究报告🏈,除了对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规模提高其道路资产基数”给予赞誉之外,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隐忧。该报告对中国高速公路规划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下一步的投资很可能包括当前交通需求不大,而建设成本较高🐈⬛,同时社会效益和联网作用很大的道路”(张弛,2007)。云南已建成或在建的多条高速公路与此类似,其社会效益远甚于经济效益👨🦼。大丽高速公路的交通需求不谓不大◾️🔰,而其在“连接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出滇入川进藏” ,甚至于“扩大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合作”等方面所显示的联网作用,以及平衡全国范围内东西发展差距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更为显著🐺。
大丽高速编号为G5611,作为杭瑞高速公路(G56)的联络线被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这一命名和编号的形式🩳,也体现出国家通过高速公路紧密连接国土空间的政治诉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速公路行业中存在划分“上行线”与“下行线”的惯例。这种上下之分并不以公路连接点之间海拔的地理高差为依据,而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向外为下行,向内则为上行。如大丽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为下行线,丽江往大理方向则为上行线,就缘于两地在全国高速公路网络中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位置关系,尽管丽江的海拔高度远甚于大理。如同大多数公路以中心城市为中心来确定“0公里”为无限延展的道路提供“标尺”一样😻,上行线与下行线之分也表达了中心与边缘的意味,实际上也是一种隐含的地域秩序,其所表达的辐射和向心的意义👌🏻,正是民族国家所强调的认同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
大丽高速在开工之际便被赋予了除交通之外的诸多意义🏑:一是大丽高速作为一种“标识”⛪️,以向外界展现云南这个西部欠发达省份迈向现代化的决心和成就✂️👸;二是作为一种诉求,是对当前“绿色发展”理念的回应;三是作为一种宣示🙍♂️🧏♀️,以表明大丽高速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目标。为此👰🏽♀️,公路的承建单位云南公投确立了“路畅人和”的筑路理念🤸🏽,并专门设立了“大丽高速公路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张文凌👤,2018),力图在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服务区、桥梁和隧道等场所展现途经区域的历史、地域、民族文化,以强化当地人对公路的认同和外来者对地方的认知🍶,隐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路”之意喻📶。
国家通过高速公路对领土空间进行规划,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全国一盘棋”的治理理念和秩序框架。在高速公路网络规划编制中,国家和省级单位着重于国土👨🏻🏫、人口、经济及城镇的布局之间的平衡🧔😽,强调公路网络的通达性、网络密度及服务水平(王成金等,2011)🙍🏻♂️,以实现保障国防安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从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可以看出,国家层面的空间生产过程被置于一种政治话语之中🧒🏼⭕️,体现出全局性、宏观性和长远性的特征。
(二)地方利益的区域博弈
在国家高速公路网络中,某一地方是作为“位置”而存在的,而位置显然是一种空间性的相对关系🎦,表达着社会文化的意涵✍🏿,使空间表现出一种层级性,“空间正义和非正义可以被看作无数与位置相关的决定产生的结果”(苏贾🦹🏽♀️,2016:44)♦︎。基于高速公路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提升地方政府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某一地方与高速公路的相对位置直接关系到资源的空间分配问题🎅🏻,因而高速公路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资源,显示出明确的经济意义。
在一条道路开始规划之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即已开始。据说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规划修建大丽公路(即省道S221线)时,剑川县领导担心公路占用太多的土地而拒绝公路经过当地,大丽公路最终避开了剑川和九河,取道鹤庆到丽江。剑川县的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大丽公路的修建极大地推动了大理🥗、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沿线区域也受益匪浅。同时,大丽公路使国道G214线的车辆大量分流👨🏼🦳,沿线剑川⚂、九河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因而,当大丽高速开始规划时,各地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极力争取高速公路途经本地。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通过高速公路而融入国家战略布局👨🏿🦱🍶,不仅能凸显地方在国家版图中的区域性地位,也能够给当地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带来重要的机遇🏃♂️,不啻为争取到一笔重要的外来“投资”🤔,对高速公路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是寄予厚望。
地方政府在国家工程中🦸🏼♂️,一方面是要完成上级行政任务。在公路建设中🔂,最为关键且难度最大的工作无疑是征地拆迁。县政府🥈、县直机关单位负责人及道路沿线各乡镇的主要领导组成了“大丽高速公路建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直接负责落实辖区内建设征地、拆迁𓀏、协调的工作。对于九河乡政府及所涉村委会的干部来说🎑,这些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由乡村干部作为一项行政任务来完成,使高速公路的“国家”意象在当地干部和群众意识中得以不断强化,更加凸显了高速公路的政治意味🍾,而配合🦟、支持甚至参与高速公路建设显然就具有“政治正确”的意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寻求地方主体价值——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早在大丽高速公路修建之前🤸♂️,丽江市和玉龙县政府便已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雄古村规划建设工业园,依托高速公路进行工业布局✯,将丽江得一集团、益华集团🈚️、玉园公司、云南白药集团等一些食品👸🏽、药材企业的工厂搬迁至园区内。
相对而言👨🏻🍳,高速公路是一个封闭空间𓀎,因而其与外部连接的出口就成为了重要的分水口。高速公路出口的设置取决于沿线城镇的经济👩🏽🔬、人口、资源等因素,也受限于公路的建设与管理成本,因而出口始终是一种资源,对地方而言又是获得某种资格和权力的入口👨🏽⚖️。大丽高速过境九河全乡30余公里内只设立了一个收费站(出口)🤦🏼♂️,收费站以九河的地理及行政中心白汉场命名,却并不在白汉场,而是设在九河乡几乎最北面的新文一村🤸🏽♂️。不难看出,白汉场收费站的选址有迁就即将与大丽高速连接的丽(江)香(格里拉)高速之意🔇,也与当地政府在相对地广人稀的九河乡北部进行新的产业布局有关。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白汉场收费站的选址不失为两全之策🏂🏼,既照顾了地方,又兼顾了片区,以这一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布局使空间利益最大化。然而,也正是这一选址决策使空间正义问题得以集中显现。
在高速公路的修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利益的权衡👏🏽,其行动与国家意志或契合或偏离🫸🏻,对于当地人的要求则或顺应或反对。实际上,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空间层面,地方政府更多地发挥着中介和过渡的作用,其以“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向当地人宣示国家的权力和意志,同时也以“地方代表”的名义争取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样一种多样的🍱、公共的🪣、积极的协商过程中,高速公路对空间的重新确分才得以完成🫷❌。
(三)乡土景观的格局重构
在乡村聚落的视域中,人们在不同空间的活动内容、频次🧜🏼♂️、意义是明显不同的🧫,进而使乡村社会中不同的空间单元呈现出特定的结构和秩序,表现出生活☺️🖖🏽、社交☹️、生计和外部等不同层次的“景观格局”(朱凌飞、曹瑀🚿,2016)。道路在乡村聚落景观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整合村落内部不同空间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沟通内部与外部的主要形式,进而与村寨的历史记忆、社会网络、价值理念密切相关。显然,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正在以一种不由分说的方式改变和重构着乡村社会的景观格局☃️,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意义🦪。
彭兆荣认为,“国道是‘霸道’🧑🏻🔧,排山倒海🤸♂️,所有‘阻碍’皆为之让路。乡土小道是平和的、灵活的、人性的、温暖的✳️,走在乡村小道上有回家的感觉”(彭兆荣👣👨💻,2017)。显然👩🏻🦰,高速公路纵贯乡野、一往无前、宏观壮丽的景象不免让人产生“霸道”之感,而其背后的权力话语和网络隐喻更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巨大冲击🧜🏻。如前文所述,大丽高速的切入将乡村道路进行阻截、改向甚或消灭,打破了九河坝子原本绵延🤥、自成一体的生产生活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区隔◀️👩🏽🔬。尽管高速公路在九河段开设了两个供人、车通行的下穿涵洞,但其对九河村落、田野、山林的切割也是显而易见的🥺,原本近在咫尺的田地可能要绕行几十公里,而原来的近邻也成了远人,不仅增加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成本💘,也切断了村寨之间的社会联结,横穿公路、路边搭车、沿路摆卖土特产的现象频频出现。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并不长,村民逐渐适应高速公路的存在🙎♀️👨🏻🦼➡️,高速公路所暗示的纪律、理性🛀🏼、分类的意识逐渐深入当地人的观念之中。
施坚雅指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40)在大丽高速通车之后⛎,九河人的商品交易基本上仍在原来的“基层市场”完成 。人们常去的几个集市是九河街(天天街)🙆🏿、石鼓街(逢3日🚣🏿♂️🤜🏿、6日♕👩❤️👨、9日赶集)和金江街(逢5日、10日赶集),每逢集日,街市上热闹非凡。实际上,由于高速公路使商品的流动获得了更便利的条件,当地人在基层市场的交易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只有在购买一些家用电器🤨、家具或农机具等大件时,九河人才会去更远的丽江市区或剑川县城👨🏼🚒。需要出远门时🌗,如果走国道(老路)的话🫣,小客车从丽江市区到九河中古村委会附近收费每人15元,到九河白汉场附近收费每人18元到20元。如果走大丽高速👋🏿,8座及以上的车辆需付37元过路费,每名乘客要多付5元车费。小客车司机通常都愿意走国道,除了��以不用交过路费外👨🏿⚖️,也方便沿路上下客。对于村民而言,高速公路的高速大多数时候并非必需,而国道的方便和省钱才是他们计较的。由此可见,高速公路上的时间与高速公路外的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节奏和结构性特征,在某种层面上,这也是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分野。从施坚雅的视角来看,当地人实际的社会区域边界并没有发生延展,反而有所收缩👳🏻♀️。鲍曼把流动性视为一种特权和社会分层的有力因素(鲍曼,2013👩🦼➡️:8-9),而高速公路并不是人们进行更大范围流动的充分条件。一般而言,更远距离的流动🐦,一方面出于个体的实际需要,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标而前往遥远的目的地👢,是建立在相对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则囿于成本♻,差旅费都是在长途出行时不得不考虑的实际问题,而高速公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出行的经济支出。
高速公路以一种难免“霸道”的形式对乡土社会的景观格局进行重构,在改变道路体系的同时,也改变了聚落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互动方式。高速公路通达远方,但实际上并未如尊龙凯时娱乐所期望的一样将当地人带向远方。从流动的角度而言,外部景观的范畴并没有因高速公路而无限扩大,在某种意义上反而缩小了🔁。
如鲍曼所言,“距离是社会的产物,而绝不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物质的‘已知事实’➜;它的长度随着覆盖它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鲍曼🐐,2013👨🏭:12)。同时🧘🏽♂️,距离的社会建构性使其在不同的行动者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进而显露出空间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国家通过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其领土空间进行规划,使政治性的空间正义得以表达🙋🏻♂️。地方政府将高速公路视为资源和机遇🤾,在发展话语之下争取经济性的空间正义。对于乡村聚落而言,高速公路是对其栖居环境景观格局的冲击和重构🕺🏿,在当地人“流动的权力”并未得到有效实现的情况下🥪🕍,难免显现出空间的非正义性。至此,更进一步的问题将被提出:在国家、地方的空间正义之下🪈,当地人将如何摆脱空间非正义并寻求空间正义?
四、寻求空间正义:九河乡村的地方性实践
高速公路对空间秩序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最先在当地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然而,正如米格代尔所指出的,“农民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接受在世界范围内对其造成严重冲击的全球经济变革和国家政策,这些过程被农民社会因地制宜地改变和重构”(米格代尔,1996👰🏽♀️:2)。在面对不公时,当地人必然会以某些行动来争取他们的利益🎛,也正因为他们在当地栖居,这种行动也就具有了寻求空间正义的意味。
(一)“弱者”及其抗争
在大丽高速修建过程中🧑🏼,对于路线规划、出入口设置方案以及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等🏃🏻♂️➡️,九河人并没有充分的话语权🎅🏿。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是因为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通过“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并且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斯科特🌏,2011:39)。
大丽高速公路及其二级连接线在九河境内总长近34公里🐃,整个工程占用了全乡6个村委会30多个自然村近2000亩的林地和耕地🐆,此外还涉及上百户房屋拆迁及上千座坟墓搬迁。因土地和房屋的测量、评估、赔付标准等问题,村民与地方政府及公路建设方多有矛盾和摩擦,他们有的甚至采取阻挠施工、偷窃建材和工具👨🏿🚒、破坏工地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此类“弱者的武器”只是村民争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大可不必上升到“农民-国家”这种宏观层面的二元对立。在反复协商之后,双方都有所让步,最终总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7️⃣,使征地拆迁工作得以完成。
村民之所以为土地而抗争,不仅仅因为其权属的问题,更在于土地流转背后的公平问题。从征地结束后村民之间的“口舌之争”和行动逻辑可见一斑♌️。失地较多的人家为征地补偿款金额远低于邻县(剑川县)而不平,他们认为国家应在如此巨大的投资中多给他们一些补偿,至少是标准一致的补偿。失地较少或没有失地的农民却因为村中(除了雄古村委会的3个自然村)没有平分征地补偿款而愤慨,认为失地的人家得了便宜就不该再抱怨。以新文一村为例,因高速公路从村东经过,村东的人家获得了丰厚的征地补偿,而村西的人家则一无所获🎤。村西的人家有时便会酸溜溜地说:“有些人家因为高速路过上了好日子🧑🧒,尊龙凯时娱乐就没那么好运了🙎🏿。”有人还会再加一句🤘🏿:“高速路搞得尊龙凯时娱乐村里都没以前和谐了。”拿到补偿款的村民大多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改善生活的计划👭,如建房⛑️、装修、买车等,一些家庭还扎堆操办起了婚礼🤰。据说九河某村当年冬天一个月内便有18对新人结婚😈👌,其中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三四十岁的“老光棍”,那个月村里基本上一直在摆宴吃酒。而在这种报复性消费之后🧏🏽♂️,很多人家对于将来的生计十分茫然。相比之下,能让未被征地的村民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们手中还有土地,在感到踏实的同时🐃,他们也期待着高速公路能够给他们带来新的、更多的机会。
对于九河乡的村民来说💂🏼♀️,土地既是其生计基础,也是生活内容📓,这是他们生存的根本❄️,也是“抗争”的唯一资本。但很显然,这种“抗争”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是个体的🛂、无组织的和非系统的,并不具有象征意义,而九河人对高速公路的期待和对政府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这种偶然性的抗争,并让他们有更强的韧性承受暂时性的“不公”。同时,尊龙凯时娱乐也要意识到,作为乡土景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土地的得与失、多与少,乃至土地的相对位置及使用方式的改变,无不对村落的秩序重构💅、社会分层、文化转型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阈限中的参与
在大丽高速修建的过程中,整个九河坝子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工地🧴🐦⬛,车水马龙、人声喧哗🏋️♀️🪖、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既失去了开工前的平和宁静,也还无法看到完工后的现代性景观,这就使工地具备了一种“之间”🏌🏽、不确定或流动的特性🧜♀️,进而成为一种“阈限空间”(Dag Øistein Endsjø, 2000)。此外,一项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完成的🧖🏼♂️,而这种零散的状态无形中增强了整个工程的“阈限”内涵👨🍳。这一空间下的个体通常处于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焦虑状态,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确定性和平衡,而参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大丽高速被划分为34个标段,九河境内散布着其中的7个标段(第23♦️、24、25、26🙋🏽、27、31、32标段)。工程队和工人按标段分别入驻当地不同的村寨,而村民通过出售商品、提供服务、获取工作机会等方式从高速公路建设中获得回报。比如,房屋出租。当地农民的住宅大多宽敞,一些房间要么空置🧛🏻,要么用来堆放生产生活用品或杂物,面对大量外来工人的租房需求,村民就将空房简单整理、隔断和装修,以每个单间每月400元至600元的租金出租给工程队。有些人家出租了3间房,每年就有15000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已经超过一个村民全年的劳动所得了。比如,出售食物。村民将自家的蔬菜、粮食,以及猪🏄🏼♂️✌🏿、鸡👽、鱼等卖给工程队,获得比市场上更为可观和稳定的收入👨🏻🍼。由于工程队的需求量较大,有些人家甚至将一部分稻田整理成菜地,而有些人家新盖了圈栏以饲养更多猪和鸡,除了满足自家和工程队所需之外👮🏼,剩余部分就送到集镇上销售💡。又如🧑🏽,集市经营🎅。工程队的入驻使白汉场的集市更加热闹,商铺、饭馆🧑🏻💻、旅社甚至修理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集镇商业繁荣。洱源清真菜馆老板娘称,2010年至2013年大丽高速公路修建期间,是餐馆经营近30年来生意最好的时候👬。有些餐馆还增设了电动游戏室🤢、台球厅、麻将室等,以供工人们消遣。再如,供给建材💕。一些有资本和有眼光的村民在附近开起了砂石场,为工地提供材料。当时九河乡境内的砂石场有8家,分布在九河(2家)🙅🏽、中古(1家)、关上(2家)、中古(2家)🤼、北高(1家)几个村,这当中有5家就是高速公路开工后新开的🧜🏼。这些砂石场,有些是九河当地人开的💒🍬,有些是外地人开的👩🏻🔧,也有些是当地人和外地人合开的。工程队很乐意将土方工程、便道维护🚶🏻♀️、材料搬运🤪、场地清理等技术要求低的工作交给村民💃🏽,借此与当地人处好关系,减少施工过程中的阻力🦑。这种零工每天的工钱50元至80元不等,村民在兼顾家中生计的情况下,每个月还能获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收入🪄。虽然大丽高速公路的修建时间不到4年,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村民们的商品意识。
在大丽高速公路修建的过程中,当地人与外来人群👩🏻💻、组织互动频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市场规则和竞争机制🤾🏼♂️👯♀️,甚至外来者迥异于当地的生活方式等都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尊龙凯时娱乐应该意识到🦗,这些工作机会对于村民的意义远不止“赚了一笔”这么简单🧜🏻♂️。一方面,这些工作让村民获得了一种“参与感”🙆🏿,有助于他们对重构中的景观格局有更为深切的认知和认同,使高速公路不再以一种“外来物”的方式突兀地存在;另一方面,当地人的主体意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包括生计的转换和未知🧎🏻♂️➡️、观念的混杂和革新、身份的焦虑和期待等,而地方性的消散和重构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主体性的生长
如前文所述🤦🏼♀️,乡村道路与传统聚落在空间关系上是互融互嵌和共生共存的💁♂️,但现代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对乡村聚落在时空上的压缩,已在某种程度上使两者之间形成了互为“他者”的关系🏞。乡村聚落失去道路节点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失去发展的机会🧡,同时还意味着其在网络化的社会体系中主体地位的衰落🔢,进而陷入某种空间非正义的境地。在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时,当地人不断调整,重新确立自我在现有空间格局中的地位和价值🚗🫁。
除了水稻、小麦🤚🏼、玉米等基本农作物之外,烤烟曾是九河农民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九河乡唯一的支柱产业,但随着整个烟草行业渐趋没落,全乡的烤烟种植面积逐渐减少🦶🏽,村民收入也随之下降。此外,在大丽高速通车后,老路上的人流量和车流量骤减,白汉场曾经繁荣的街市日益萧条,大量商铺纷纷关张,地方集贸经济的路子也行不通了👔。一些年轻的村民曾应聘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做收费员,2015年8月白汉场收费站37名职工中有6名本地人,但不久之后即有5人先后离职🍦,到2016年9月只剩1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地人已经慢慢失去了对高速公路的热情和期待,同时也喻示着当地人正在适应高速公路带来的冲击,逐渐找到新的机会。
2010年九河乡金普村普米人张某在熟人介绍下接触到一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高山植物——山葵👩🏿🍳,便尝试种植🦜。试种成功后🙍🏽♂️,张某在2013年8月成立了金普村山葵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又于2014年5月注册了普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九河乡以及石头乡、龙蟠乡等周边乡镇的150多家农户合作,根据日本客户的订单每年种植700—800亩山葵。公司雇佣当地人在关上村占地15亩的基地对山葵进行初加工✤,经大丽高速、楚大高速🔧、昆楚高速运往昆明,在昆明的食品厂进行深加工后直接出口日本。九河甸头村白族人杨某于2015年在自家后山山坡上开了一家养鸡场👨🏼🏭,由于大丽高速公路路面排水出现问题,养鸡场被洪水冲毁。2016年初杨某成立了靠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紧靠白汉场收费站的新文二村租下一片林地放养肉鸡,其生态、绿色🧑🏻🔬、无污染的产品备受丽江🦧、中甸👩💻、大理等地市场欢迎。此外,一些种植中药材、芥末🧓🏽、魔芋,养殖黑山羊🤥、黑毛猪、蜜蜂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纷纷成立。它们将当地的气候👋🏻、土地、物产的优势充分发掘出来,获得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𓀋。同时🛠,高速公路也为活禽🎅🏼、活畜及新鲜果蔬的运输开通了“绿色通道”,减免过路费🤗,为当地农特产品快速进入外部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九河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走向外部市场,使其以出发点和中点的意义重新获得大丽高速节点的空间地位🩵。同时🤸🏻,这些合作社以合作突破了家庭🚐、村落和族群之间的界线,形成新的联合🗑,以集体的方式争取到了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使地方意识重新形成,在高速公路重构后的乡村聚落景观格局中生产出新的地方主体性。
可见🅾️,九河人所说“高速公路一修通,尊龙凯时娱乐这里就变成真正的山区了”,实际上是对丧失发展机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担忧👩🏻🦼。此种“边缘空间”不仅表现为某种独特的空间类型🍷,“还体现出属于这个空间区域的个体、群体、活动、话语、权益➞、感受力的诸多特征”。(童强,2010:93)。他们为此进行抗争、积极参与、自我调适🛷,以坚定强韧的精神和实践来寻求空间正义。这些努力不仅使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的回报,更使他们看到了希望,获得了信心,并为处理乡村聚落与地方发展🤹🏼♀️、国家规划乃至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积累了经验👥。
五、结论
福柯以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来分析、描述与阅读不同形式的空间🙋🏽♂️,其原则之一就是差异地点(heterotopia)和差异时间(heterochronies)的相关性,除了“存在着一些无限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尚有那些以其最瞬间的、转换的🧛🏿♂️⭐️、不定的时间对应……的差异地点”(福柯,2001🚶♀️➡️:25-26)。聚落的地方性意义源于长期的历史累积⚈,可被认为是前者,而道路的流动性价值在于短时的传输过程,可被视为后者🛖🛹,二者分别表现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不同面向。“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现代性的时—空特性的意义主要是非连续性🧏🏼♀️、断裂性、非确定性和风险性♑️。”(景天魁🛷,2015)当聚落与道路这两种差异地点并置于同一语境之中时,空间转换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无限张力将充分显现🪧,并因其差异而必然引致关于正义性的讨论。
空间正义或非正义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问题🧑🔬,有其形成、凸显和消解的过程,在不同的行动者视角下也可能展现出各异的面向。正如尊龙凯时娱乐所看到的,历史悠久的乡村道路具有一种自然平和的特征,道路与乡村聚落互嵌互融😧、相生相长🦸🏼♀️,使城乡之间因普遍和持续的互动而形成一个连续体🕛,空间正义的问题是潜隐的🧑🏼🍼。近代公路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色彩🕑,展现并实践着国家的意志和权力,使乡村聚落不断向道路趋附,展现出“中心”对“边缘”的吸附🕺,空间正义的问题开始显现👩🏼🏫。高速公路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质😆,这是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主义语境下地方经济竞争的重要资源。但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使乡村聚落被区隔和忽略,使当地人有一种被遗弃和被排斥的感觉🚾🍗,由此而使空间正义或非正义的问题成为焦点。面对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所凸显的问题,当地人通过消极抗争🤟🏽、主动参与、积极调适等方式寻求空间正义,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希望🐂、信心和经验,进而也使地方的主体性得以不断增强。当地人对高速公路的进入𓀆,同时也是高速公路对乡村聚落的融入。高速公路在乡村聚落的本土化👨🏿🦳,喻示着空间非正义的不断消解与空间正义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蓬勃发展正是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科技进步的表现🌼,反映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也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及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空间层面凸显出来⤴️。2014年3月🍡,习近平作出“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指示。2017年12月🤛🏽,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可见,农村公路的建设对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要推动“四好农村路”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的保障,就要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使乡村道路体系与高速公路网络形成有效连接和互动,消除空间区隔和地理不平衡,形成乡村与城市的真正联结与连续🏌🏻♀️。同时💇🏼,要注重发挥地方、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使道路空间的变革和重塑不纯粹受制于外来力量,也能够反映当地人的诉求,进而在空间意义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道路的实质是一种通道🧑🏼🏫,对于社区的价值就在于沟通内部和外部👩🏻🍼,而所谓‘外部’是可以无限延展的,甚而扩充到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朱凌飞,2014)即使尊龙凯时娱乐只是在聚落中讨论道路🚞,全球化的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全球化种种过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鲍曼,2013:3)。当乡村聚落因为不断改变的道路景观而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时,其所面对的空间正义与非正义问题将更为复杂和多样,需要尊龙凯时娱乐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