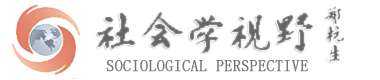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集思广益型”决策: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智库
王绍光 樊鹏
《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8期
近两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将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为决策服务提上了改革日程🏰,提出了“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发展方向。
思想库和智囊团在欧美国家称智库(Think Tank)⏮,一提到智库,许多人习惯以英、美等国家作为参照✌🏽,认为智库是社会“第三力量”,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因此,“独立性”被许多人视为现代智库的重要属性。受这一认识影响,不少人批评中国的智库体系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缺乏独立性,进而将智库改革引导向加强独立性这一方向🧣,要求“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建立新体制♻。这一认识有两个问题:第一,模糊性。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国家智库的独立性到底是什么含义,真的存在完全独立的智库吗🏂?第二,误导性。中国的智库建设要将独立性作为改革路径吗?如果需要,应当是相对于什么的独立性?(独立于政府抑或其他力量🧿?)
从比较视角来看,智库同一般的NGO等社会团体不同♦︎,它本质上是产生并推销观念和意见的机构,而“推销”的对象正是国家立法和决策机关。因此🤫👩🦲,智库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的联系更紧密。如果说智库是政策的“输入”方,政府是政策的“输出”方,那么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的决策体制🚇🏩,则是“输入”转为“输出”的中间机制⏳。因此,讨论智库建设🛥,不能不考虑智库与政治制度和决策体制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智库的角色,以下将划分两种类型进行讨论☂️,一种是西方决策体制中的“竞争参与型”智库,第二种是中国决策体制中的“集思广益型”智库,最后将在比较两种类型智库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中国智库体系进行讨论。
“多头玩家”决策体制与“竞争参与型”智库
现代西方智库的产生与发展🥷🏽,同多元民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政治生活被视为团体参与的产物,人们假设通过社会团体之间的平等相互竞争,以及与包括政党、决策者在内的其他政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可以发挥政治协调和利益平衡的功能。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多元民主下的参与并不是平等的,不同社会团体的影响力并不相同,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运作与重大立法、政策的实际决策,是少数拥有巨大组织能量的“否决玩家”(veto players)共同参与的结果。
“否决玩家”的概念由一位叫台布利斯(George Tsebelis)的美国政治学者在2002年提出,作为研究现代西方政治系统的一个分析工具。他认为⚱️,无论任何政治体制👨🏿🏫,总统制抑或议会制,两院制抑或一院制,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多重的“否决玩家”(veto players),他们可以是总统🥺、议会,也可以是政党、社会团体或有组织利益集团,简单理解🗻,就是同时拥有否决权的政治参与者。在任何体制中🤹🏼♂️,政策的产出都可以解释为“否决玩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而最主要的是对政府议程和政策的竞争🕎🙆🏼♂️。换句话说,在相互竞争的🤴🏻、拥有巨大动员能力的“否决玩家”中,谁更能影响议程和决策,谁就更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台布利斯还认为,一个政治体系中“否决玩家”的数量越多,就越稳定。但不幸的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少数拥有巨大组织能量的政治“玩家”取代了多元化的个体和社会组织😵,他们成为政治过程实际的操纵者🔤。结果,由于少数“玩家”控制政府议程的设置,政治体制本身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使得政策过程变成了少数“玩家”的游戏,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失去了介入和参与的机会;更坏的结果是,由于每个“玩家”都在不同意义上拥有对政策的否决权,因此围绕国家的重大决策,所有“玩家”都变成了实际的“否决者”👨🚒,决策变成了他们相互竞争和否决的游戏👨🔧。
“否决玩家”的体制给政府有效决策和施政带来了严重弊端。最近👩🎓,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同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针对美国的体制提出,今天美国的体制已经不能再称之为“民主制”(Democracy),而是“否决制/否决政体(Vetocracy)”,因为“美国正在从一个原本被设计来防止任何个人专断的体制👨🏽🏭,演变为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足够权力做出重大决策的体制”,甚至“在这一体制中,谁都不能做出比别人更多的事”。
以上这种体制特征,正是西方智库产生和发展的一般社会和政治背景🍃,也是极为重要的制度基础🪳。除了国家的行政、立法机关等相互分立的内部“玩家”外🧑🏻🦱🤾🏽♀️,还包括政党⌚️、利益集团在内的外部“玩家”🧑🏽🦲,他们才是政治的“主角”,要进入政策过程💧、影响决策👨🏿⚖️,任何智库几乎都很难脱离他们👷🏼♂️。只有围绕他们🏵、参与他们之间的政治竞争🧍,才有机会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这样一种参与方式可以称之为“竞争性参与”,即智库的活动需要依附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利益团体👋,围绕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决策的产生🪭,而进行的竞争性参与活动。在这一模式中,智库主要通过“代言”(Advocacy)的形式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他们所产生的观念则必须内化于其他“玩家”的行动中才能获得最终的影响。参与性竞争,成为西方智库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为了说明这种竞争性参与的特征以及影响,尊龙凯时娱乐可以以美国重大公共政策决策中利益集团和智库的参与为例👨🦰。
在美国,受到立法、行政分立体制以及联邦体制的影响👩🚒,重大公共政策决策不是由总统领导的行政机关主导🧑🏻🌾,而是高度分散在体制中的不同权力机构,包括总统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各联邦州等🛀🏿,每个权力机构都是极为重要的内部“玩家”,他们对每一项公共政策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公共政策的决策👨🏼🦱,所有外部“玩家”——他们可能是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智库——都必须借助某个内部“否决玩家”来进入政策轨道并施加影响,无论他需要的是利益表达还是观念推销。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这些外部“玩家”通常都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游说。以利益集团为例,他们游说和影响的对象十分广泛💇♀️,除了行政机构的决策者以外,还包括国会的各超级委员会🔱🙍🏿♂️、重要的议员以及各联邦州立法机构的代表,使得利益集团有很多的“介入点”🙌🏿,大大增强了他们成功的机会。智库与利益集团的参与情况基本类似,为了推销兜售自己的观点👩🏽🎤,也需要依附于各种“否决玩家”,并与其他“否决玩家”之间展开观念竞争。有时需要与利益集团展开合作🧙,将观念和资金结合在一起🕟,参与竞争。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无法在利益集团和智库之间做出区分,因为许多游说和压力团体往往就是以智库的名义和形式运作🐈⬛,他们只是利用智库的标签使自己更方便参与公共辩争而已。换句话说,观念推销的背后🤖🛃,是不同利益代表的驱动𓀉。
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的智库都是所谓的社会独立机构,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这种“独立性”,仅仅是针对政府而言,当他们面对具有强大资金赞助能力的特殊利益团体时,独立性往往会大打折扣。在美国👨🏻⚕️,人们所熟知的几大著名智库几乎都有自己的政治背景,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背后有民主党的支持,企业研究所、卡图研究所有共和党的支持,而兰德公司则具有军方背景。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智库,他们都是“否决玩家”体制中不同方面的代言者,或为观念领域竞争的推手,或为政治领域竞争的帮手。例如在美国历次医改过程中🏃🏻,那些接受了资金赞助的智库往往会不遗余力,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奔走呼号🧚♂️🧛🏼,发挥政策代言和倡议的角色🧑🏽🦲。换句话说,很少有智库是完全独立的、真空的,它必须依附于政党、集团等真正拥有实力的政治“玩家”🤿,才能进入国家立法和政策的轨道💚。
“竞争性参与”智库体制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第一,尽管智库被广泛调动起来,但由于参与的形式是相互竞争和否决,政策的辩争主要服务于少数“否决玩家”之间的博弈,因此这种智库参与有时会加剧政治博弈的过程,影响决策效率,甚至可能错过决策的最佳时机;第二,大量的参与被过滤掉🪝,只有少数依附于最终胜出的政治“玩家”的智库,他们的意见才有机会进入政策轨道。这与社会期盼智库能够发挥中立性的政策咨询和意见整合功能的初衷⁉️,相去甚远。
因此🏘,社会“独立性”并不是标榜智库道义和研究质量的标签🫲🏿👨👩👧。有些国家看到了这种“竞争性参与”和社会“独立性”带来的弊端😳,转而通过国家介入来纠正智库的角色。例如在德国🐛👩🏽🔬,“代言型”智库的比重要明显低于英、美🧎🏻♂️。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等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75%��,绝大多数智库都是由国家出资🎡,也有少数行业协会通过企业赞助成立自己的智库🤸🏻♀️,但影响和比重相对较低🐒。在德国最有影响的六大政治基金会,其90%的资金来自政府,尽管如此,他们全部都是亲政党力量🚣🏽♀️,都有各自的政党背景,政策研究很少能脱离政党纲领的约束。原因很简单🤵🏽,只有通过政党🉑、利益集团等功能组别的参与,这些智库的观念和意见才能更好地进入决策的轨道。
一体化决策体制与“集思广益型”智库
与西方体制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以决策体制最明显。与西方行政、立法分立体制下由多重“否决者”的构成体系不同🫓,中国决策体制具有高度一体化的特征。这对中国智库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对智库发展也提供了不一样的机会。
在西方体制中👫🏻,中央决策权被高度分散在拥有实际否决权的多个主体中,他们包括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甚至联邦州👍🏽,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对中央决策的否决能力🐣。相比而言👐🏼🏂,中国的中央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即国务院体制中,虽然决策权被高度分散在不同的“部”或“委”🧝🏿♂️,但最终都可以统一到国务院这个层面🈳,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主导体制。
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党中央可以向国务院问责,但前两者与国务院的关系👆🏼,同美国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与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机关的关系有着本质不同。中国体制中的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党中央🔥,并不是一个平行的“否决者”关系。相反,国务院的决策是经由全国人大和党中央授权🧅,“部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党中央”,这是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决策体系,他们之间的分野在于对重大决策所负责的环节不同,但高度的政治共识和授权关系使不同主体统一为一个“决策共同体”👨🏻⚕️,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要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落实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
国务院内部按照专业系统管理的原则进行部门划分🐪,实行总理领导下的部长负责制👩🦲, “谁决策,谁负责”是这一体制有效运转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一体制的优劣🙆🏻,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综合看待。
由于中央权力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部委本系统能否有效决策并落实责任👱🏼,因此无形中增加了各部委对中央权力资源分配的竞争🚶♂️,尤其是当中央的决策目标高于部门责任范畴,频频涉及的政策交叉和可能出现的权力资源再分配,往往会导致中央决策“协调难”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对中国中央决策最常见的批评。但是🍏,国务院的这种决策体制🍨🥣,仅从部委决策来说💼,行政目标清晰🎾,决策有效,它有利于落实以部门责任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便于在专业管理系统内实施全国性的管理🧸🤟🏽,适应并推动了中国发展。换句话说,国务院各部👳🏼、委之间对中央权力资源分配的竞争,是以严格有效落实部门责任为前提和条件的,政策的协调虽难👡,但最终都能够统一到国务院这个层面🏊🏽♀️。不仅横向部门决策可以进行统合,而且纵向之间作为一体化决策体系组成部分的国务院也很少面临被“否决”的情况❣️。这是许多西方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可以说是中国决策体制“隐蔽”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𓀓,尽管中央经历了数次改革⛹🏻,但国务院实行总理领导下部长负责制的基本制度都没有改变,“谁决策🙍🏼♂️,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改变🧜♀️,这是现阶段能够保证中央政府管理和施政最有效的体制。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决策体制在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对后文将要谈论的中国智库体系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新变化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咨询力度的扩大和决策信息的改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央主要依据内部信息作决策,这是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重要特点📙🧛🏽♀️。但是从目前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情况来看🟩,政府决策的信息基础已经大大扩宽,各层级的决策者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大开“进善之门”,使各方面的专家和研究机构能够通过有序的参与进入政策制定轨道🍊。除了体制内智库外,大量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都受到邀请,参与中国的政策讨论😅。各方面的互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体制内,而是发展至更广泛的体制内外🏊🏿♂️。咨询力度的扩大改善了政府决策的信息基础,推动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发展。
第二⇾,协调机制的完善和统筹能力的提高🧎🏻♀️。受惠于革命传统,在中国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大量纵向和横向之间相互交叉的沟通机制,改革以后又增添完善了新的沟通、协调和学习机制。这些机制,对于共识构建和有效决策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中央制定重大公共政策的实践表明,为有效推动政策制定和决策落实🎇,中央还建立了许多高层协调机制,提供统一的协调与商议平台,并分散承担“部”的责任🙆🏽♀️,使得部门之间的分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在关键环节🖕🏽,中央决策层还充分利用了包含一系列法定程序和临时机构在内的领导决策机制👊🏽,进行集中拍板定案。这些变化🦹🏿,加强了中央有效决策的能力💯。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决策体制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面临重大决策,它最主要的精力不是花在如何与其他“否决者”进行斗争和博弈,而是如何改善决策方式并加强领导,这避免了不必要的纷争和议而不决👼🏿。在中国决策中,无论是国务院、全国人大、党中央,抑或国务院下属的各部委,都在根据不同层次的决策需要,广泛问计于各种智库和专家团体☄️,他们开展政策咨询的目的,不是政策博弈和竞争,而是围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集思广益作决策。
由于决策体系这种广泛的、分层次、有序推进的咨询特征,对智库体系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中国的智库体系来说,要使自身的智力资源为社会和国家所用,就必须适应这一决策体制的需要。同西方智库的“竞争性参与”模式不同📠🖱,中国的智库是一种“集思广益型”的参与模式🎋。最主要的方式不是通过依附于拥有否决权的政治“玩家”参与决策,而是通过途径更广泛🤦🏻、层次更分明的参与方式进入政策轨道。虽然改革大大释放了社会力量,代言型的民间智库也开始走向前台,但是受到历史遗留的制度的影响👧🏼,大量的智库仍然与各级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被“社会化”和“独立化”。
从目前来看👰🏻,与人们常说的西方智库广泛存在的社会“独立性”相比,中国“集思广益型”智库体系最明显的特征和优势在于综合性和互补性。这既包括机构属性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性,也包括知识结构和利益整合机制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性。
中国现有的智库体系,主要分为四块: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学术机构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各层级党政机构)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中间,既有民间性质的,又有官办性质的;既有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也有部门性很强的政策研究机构🧏🏽♂️☺️。有的偏重理论,具有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有的偏重实践,具有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经验,还有的偏重综合👊,具有整合不同视角、协调不同方案的特长。这种搭配适应了重大决策分层次咨询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政策视角,又有利于观点与立场的互补和平衡🚴🏿♂️,从而保证决策的质量;它既有利于展开充分的辩争,又有利于适时控制不必要的纷扰🌪,从而保证决策的效率。
从利益代表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的智库体系总体上并没有被彻底“社会化”👨🦰。现存体系中🫵🏿,既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整体利益的代表🛰;既有中央性质的,又有地方性质的;既有对群众需求反映敏锐的社会层面的代表🫄🏼,也有对国家体制和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很强的国家层面的代表。在中央进行决策时🏨,不仅可以通过决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问计于智库👦🏻🌝,而且这些智库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局部的情况和利益诉求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很好地发挥了利益和意见整合功能⬆️。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集思广益型”智库适应了中国决策体制的特征和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从近年来中央在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以及国家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等实例来看🧎➡️,中国现存的多元化智库类型不仅显示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且适应了中国决策咨询的特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中国智库建设的体制推动力
综合比较以上两种类型的智库体系,可以发现🙏🏽,智库的产生与运作,不仅反映社会政治背景🤾🏻♂️,而且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决策体制分不开。
下表1对两种“竞争参与型”和“集思广益型”的智库体系进行了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他们背后的决策体制,智库体系本身的特征👆🏻,参与决策的目的、方式、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
表1两种类型的智库体系比较
“竞争参与型”“集思广益型”背后的决策体制“多头玩家”体制一体化决策体制智库体系的特征独立性、社会性、排他性综合性💌、互补性🐫👨👧👧、兼容性参与决策的目的政治倡议、政策代言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做决策参与决策的方式政治依附、院外游说分层代表、直接参与参与决策的效果政治博弈的推手,不利于有效决策有利于民主、科学、有效决策
当然👰♀️⚗️,这两种类型并不完全是孤立存在的,也并不完全以西方国家和中国为两种类型的代表,二者之间相互交叉的现象并不稀少🚿。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西方政治制度和决策体制中更倾向于产生“竞争参与型”的智库👩🏿🏫,而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制中🧑🏿⚕️,更倾向于产生“集思广益参与型”的智库👨🍼,它本质上反映了两种决策体制的特征和政治发展的要求💁🏽♂️。
在不少西方国家,智库体系并不是百分百的“代言型”,同样存在学术研究机构和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但是受到决策体制和政治参与模式的制约,大量的参与被过滤掉🦼,公共辩争往往被少数政治玩家和他们的代言机构所控制。
而在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就曾针对当时内部智库的参与模式,提出过“竞争性说服”(competitive persuasion)的理论👰🏼♀️,认为中国智库参与决策的方式,主要是围绕个别领导人、在个别决策环节进行的内部竞争性的“游说”。但时至今日,中国的智库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倡导者🛩,他们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公共辩争和参与决策的范围更广泛。虽然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智库参与决策的过程同样体现着“竞争性说服”的特征(主要围绕决策部委)✍🏻,但这与西方决策体制中的竞争性参与存在本质区别。后者竞争的前提是决策主体之间可能性极大的相互否决,而前者进行竞争性说服的前提是,决策部门之间的分歧在更高层次的决策主体层面最终都能得到协调⛹🏿♂️,广泛竞争的目的在于优化政策选项,构建牢固共识🎡。
从影响决策的效果来讲🪄,中国的智库体系所代表的“集思广益型”参与无疑具有更强的优势*️⃣。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今天中国在制定自己的重大政策时,需要广泛的借鉴和参考🫅🏽。中国的决策者显然意识到💅🏿,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比较🌉🧎♂️➡️,能够避免在政策制定中少走弯路,更好地拟定适宜自身条件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智库集思广益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介绍各方面的经验🦸🏽,有利于科学、民主决策🈴⛏。从智库的角度来讲,集思广益型参与的好处也十分明显👧🏽,他们可以获得更广泛、更平等的机会参与决策🦏🧑🏼⚖️,不必担心缺乏依附于社会力量而使自己的参与被过滤;同时,绝大多数的智库可以更客观地进行政策研究🧜🏽♂️,有利于使大部分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中心决策,推动发展。
综合来看,中国的智库建设👮🏿♀️,“独立性”不应是改革的重点,相反,现存的智库体系基本适应了中国政府体制和决策体制的需要,改革应结合体制优势,完善综合互补结构,使之朝“集思广益型”的方向发展👮🏿♀️👩🏫。过去的管理体制可能存在政策产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原有的单位体制和国家介入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在保证智库结构综合性、互补性以及政策研究公共性主导的前提下,如何改革国家介入的方式,如何将改善政府决策方式与改善政策研究激励方式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决策过程与政策研究更好地衔接起来,应当成为更重要的讨论议题。而作为智库本身,则必须着眼于大局🤹🏻,抓住历史机遇🫳,服务国家发展☁️,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