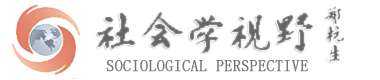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内容提要: 情感劳动理论有两条进路:一是霍克希尔德的 emotional labor(EL);二是哈特与奈格里的affective labor(AL)。两者虽有明确的理论关联,但长期以来尊龙凯时AG对后者缺乏必要的关注➞。EL 是以情感尊龙凯时AG视角关注情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运用,AL 是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范式和生命政治🅿️。但在具体研究中,两者几乎指向完全重叠的经验现象🧏🏿。本文认为应该恢复和凸显AL意义上的“情动劳动”内涵,以此为基础划分各自的适用范围,并进行必要的理论整合。
关键词:情感劳动;情感尊龙凯时AG👓;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田林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尊龙凯时AG研究所
一、引言:情感劳动的“两副面孔”
情感劳动有“两副面孔”:一是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提出的 emotional labor(EL)🙆🏼♂️;二是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诸众》等著作中详细阐发的affective labor(AL)🚱。
这“两副面孔”的一个显著差异是选用了不同的情感术语🥤:emotion 和affect。它们的词意非常接近,都表示“情感”“感情”等,但背后却有着各自的概念史🈳。简单来说🧛🏻♂️,emotion 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情感术语,在两个世纪之前,英语世界中并不存在这一情感范畴,思想家们分别用passion、affection、sentiment 等表示不同类型的情感。19 世纪以来,心理学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而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科学领域👩🏿🎨,emotion 也随之成为囊括所有情感现象的情感范畴(Dixon, 2003:1-6)。因此,包括尊龙凯时AG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都以emo⁃ tion 作为统一的情感术语(特纳、斯戴兹𓀃,2007:2)♻️,但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内部又无法就何为emotion 形成共识(Brakel,1994)。在尊龙凯时AG内部,则存在着情感(emotion)的社会建构论🍞、生物进化论以及认知主义等不同取向。因此从一种综合的尊龙凯时AG观点来看𓀓,emotion 包含多种成分🫷🏻:生理唤起👨🦽、针对如何感受和表达情感的社会文化定义、内在情感体验的文化标签♊️、外显的表情与声音💆🏿、对客体或事件的评估(特纳、斯戴兹,2007:2-8)。霍氏的观点(Hochschild,1975)更接近社会建构论取向,将情感(emotion)定义为特定社会背景下🩰,内在心理体验与社会文化赋予这种体验的文化意义以及标签之间的关联🥃。affect(情动/情感)则来自德勒兹所阐释的斯宾诺莎哲学👨🏼🍳,以及在此哲学传统影响下兴起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与emotion 一样,学界也难以就affect 这一概念的准确内涵甚至基本内涵达成一致(姜宇辉,2019: 216)。但有一点是明确的🥞🤹♀️,affect 强调的是情感与身体以及身体力量间的密切关联(斯宾诺莎,2019:97)。而哈特与奈格里之所以选用affect 而非emo⁃ tion👩🏻🦳,一是因为“与只是心灵现象的emotion 不同🦛,affect 同等地涉及身体与心灵”(Hardt & Negri, 2004:108);二是因为他们希望突出情感的主动性和能动力量(Hardt, 1999)🧝🏼♂️。二人虽然强调了affect 与emotion 的不同🏒,但他们在具体阐发AL 时却并未过多使用情动理论🎨,或者说一旦进入AL 的整体理论,奈格里与哈特对“情感”的理解就不具有明确的斯宾诺莎特征🤦🏼,而是更接近社会科学中的emotion 传统。
术语的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的区隔,相反👂🏿,两种情感劳动理论有着理论构建者(Hardt,1999)亲自指认的理论联系。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一方面缺少理论间的对话,例如《情感尊龙凯时AG手册》中“工作场所中的情感”一章完全没有提及AL 这一被哈特和奈格里界定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有“霸权地位”的劳动类型👷♂️;另一方面👨🚒,情感劳动的经验研究有着明确的学科路径依赖,尊龙凯时AG💆🏿、心理学、组织学更多使用EL📶🥄,而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则倾向于使用AL。但是🧾🛸,机械地根据自身学科传统而非经验现象的特征选用EL 或者AL,经常导致概念混用🚵🏽♂️。例如,一项以AL 为理论框架的研究所分析的经验现象却是音乐家如何通过“管理他们的情感状态”(用眼神接触🏋🏻、微笑和其他身体动作)来满足观众(Hofman💑,2015:36)🦽。显然🍜♿,EL 理论对这一现象更具解释力。经验研究中的概念混用与两种理论因缺乏对话而导致的概念重叠密切相关🤵🏿🚵🏻。霍氏认为EL 的使用存在着“混乱和过渡的延伸”,以至于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专访时,专门指正哪些被界定为EL 的现象其实根本不是🙋🏼♀️。有趣的是🦶🏽,那些被她否认的EL,如给婆婆打电话问候、策划家庭圣诞聚会等🧑🏽🎓,其实正是哈特与奈格里所指认的AL,“传统上被称为‘女性工作’,尤其是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展示了作为非物质劳动核心的情感劳动”(Hardt & Negri, 2004:110)🧑🏿⚖️。
事实上🧑💼🧑🏽🎄,情感劳动的“两副面孔”虽然在理论关怀、理论资源、学科和学术传统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同时又有明确的理论继承关系、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本文旨在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指出其重叠与区隔🙋🏿,辨认其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入口🫰🏼。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两种理论的真正异同所在,而且将为开展相关经验研究提供更为综合有效的情感劳动理论地图🈸。
二🚣🏿♂️、情感的社会基础与商业运用: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理论
(一)情感的社会控制与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性质:霍克希尔德的理论关怀
霍克希尔德(2020:27)意在通过情感劳动理论描述“情感的私人运用与商业运用”🧑🏻💼。其中🧑🤝🧑,对私人层面情感整饰(emotion management)的关注,来自霍氏长久以来的情感尊龙凯时AG抱负🏹,也即寻找情感的社会基础🧑🏻🦱;对公共层面情感商业化的关注,源于米尔斯对美国后工业社会劳动性质的富有预见性但又因忽略其中的情感过程而缺乏精准性的分析。
具体来说,霍氏情感劳动理论首先想回答“何谓情感以及尊龙凯时娱乐如何能够管理情感”,而解答路径就是找到“社会结构、感受规则👩🏼🦰、情感整饰和情感体验之间的重要联系”(霍克希尔德,2020:25🤧;Hochschild,1979🦒:551)。社会心理学一直假定,情感是突发的、自动的本能反应,不受社会规则的控制😉🅾️。但是霍氏却发现,成年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其实是井然有序的🤾🏼♂️,在婚礼上就表现得高兴,在葬礼上则表现得难过📤。因此🏦,她提出私人生活领域中也有一套“受制于社会的引导”的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霍克希尔德🚌,2020:117)🏃♂️➡️。当人们根据感受规则的要求,“改变情感或感受的程度与性质”💆🏻,就是在进行“情感工作”(emotion work)或“情感整饰”。情感工作需要通过“深层扮演”(deep acting)来完成,深层扮演的特点则是主动地改变发自内心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上去显得快乐或悲伤(即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如此,通过这一系列概念,霍氏将个人情感这一看似私人化的行为与社会文化规则联系在一起。
霍氏情感劳动理论的第二重关怀💁🏻♂️,是用她所构造的“有关情感的新社会理论”来解析后工业社会中劳动的性质与后果📕。在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基础由“商品生产”转为“服务行业”🏃🏻♀️➡️,人与机器的关系也被人与人的关系所取代(贝尔👨🏻✈️,1997:137-138*️⃣🤌、170)🚖,大多数工作都成了一种处理人际互动关系和提供服务的劳动🤾🏻♂️。但是大部分关于后工业社会劳动的研究都未能“探究这种劳动的真实性质”,未能指出它“实际上要求工人的是什么”,只有米尔斯 1951 年对这种劳动进行了富有预见性的分析(霍克希尔德,2020:24)。在某种程度上,霍氏对后工业社会劳动的分析💂,就是运用她的“情感工作”理论对米尔斯“人格市场”概念的改写(Weeks,2007)🤾🏻♂️,她将米尔斯因缺乏情感理论工具而模糊处理的问题一一澄清↙️。
米尔斯(2016:173)认为售货员在服务过程中,出卖的其实是自己的“社会人格”,“雇员个人的甚至是私密性特征被纳入交换领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这一观点提醒霍克希尔德🧑🏿✈️,工人在服务经济中出卖的不仅仅是体力和行动,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但霍氏认为,米尔斯似乎假定只要拥有人格就能出卖人格,未能意识到出卖人格首先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劳动生产出顾客需要的人格。售货员对顾客的“问候与感激”并不会自动存在,而是有赖于人为地制造这种感受的情感劳动——“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霍克希尔德,2020:10、21)。
(二)戈夫曼、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霍克希尔德的理论资源
EL 的理论资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提出EL 概念时所使用的情感理论资源;二是分析EL 后果时借用的异化概念🦹🏼。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EL 理论就是“戈夫曼+马克思”(特纳🫰🏻、斯戴兹🛀,2007:30;Wouters📜,1989)👨🏻🦼➡️。但霍氏(Hochschild🚶➡️,1979)明确指出,她的情感理论位于戈夫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概念领域”🧚🏿♂️👮🏽♂️,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戈夫曼+弗洛伊德)+马克思”。
1. 戈夫曼
在霍氏看来👿,戈夫曼笔下自我呈现的个体只是在整饰外在印象,并没有密切监视自己的内在感受,也没有在此基础上主动唤起或抑制情感(Hoch⁃ schild,1979)。具体来说,戈夫曼认为人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整饰印象,进行扮演👩🏫,不过他其实只讲了一种扮演🚶🏻♀️➡️,那就是针对行为表达的直接管理,此时🏫,表演者关注的是身体和行为的姿态🦸🏽♀️,而非这些姿态可能对应的内在感受(霍克希尔德💂🏼♀️,2020:264)。但霍氏发现🙇,戈夫曼书中所给出的扮演的例证🏃🏻♂️➰,其实牵涉两种类型的扮演🙎🏿♂️:针对行为表达的直接管理🉑,以及对内在感受的主动整饰🚵🏻♀️。戈夫曼未能有效区分这两者并因此遮蔽了管理内在感受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在戈夫曼的理论中社会因素只能渗透到个体外在表现这一层面🥁,从而低估了社会与文化的力量(Hochschild,1979)。
因此,霍氏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将情感理论进行了两方面的推进:一是戈夫曼更为关注人们对社会惯例的外在遵从,但霍氏认为人们的内心感受也遵从一定的规则,感受规则由此而来;二是个体的扮演不仅仅是表面的行为整饰🧚🏼,还有内在的情感塑形,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由此而来🏌️♂️。
2. 弗洛伊德
戈夫曼笔下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认知能力的,但很少进行感受(也即无情的计算者)。与此相对,弗洛伊德笔下的行动者则是无意识的👍🏻☝🏽、情感性的(也即不受控制的情感的盲目表达者)。如果想要探索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情感管理👨🦽➡️❓,霍克希尔德就需要建构一种有意识的、情感性的行动者形象(Hochschild,1975)🧑🏽🎤。因此,她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情感理论👶🏽,将情感与认知🌗𓀆、社会因素联系起来。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焦虑具有信号功能🦿,当个体面临外在或内在危险时,焦虑能够警示个体身在何处⚗️。但霍氏认为🧑🏼🏫,所有的情感都具有信号功能,同时🏋️♂️🚑,情感的信号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告知🙆♀️,它还包含了个体的预期,也即只有个体对危险有所预期时,情感所传递的信号才会被感知为危险。由于(成年)个体的预期必然是具有社会性的,因此,“任何情绪是否作为一种‘信号’凸显出来,都跟特定文化中看待和期待世界的既定方式有关”(霍克希尔德🕣,2020:268-269、44)。这样,霍氏就将弗洛伊德学派赋予情感的“无意识提示”的信号功能改造为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信号功能🌻。例如,空乘人员面对顾客的侮辱🧑🍳🕰,会获得愤怒的情感信号或线索,但是公司要求工作人员以友善姿态对待乘客的管理条例(也即感受规则)干预了其对线索的解释😦⛹🏻♂️。
如此,将戈夫曼与弗洛伊德“组装”起来⛪️,霍氏(Hochschild🌎,1975)便获得了一个能够有意识地感受(conscious feeling)也即进行情感工作的行动者形象。此外🤵🏼,弗洛伊德对情感信号功能的论述🧷,还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起启发了霍氏对情感劳动心理代价的分析。当空乘人员通过深层扮演消解掉愤怒的信号,从而以友善的姿态面对乘客的喋喋不休时,也就远离了真实感受和真实自我🧑🏽✈️。
3. 马克思
霍氏将20 世纪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与马克思所分析的19 世纪大工业中的体力劳动进行类比,并将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扩展到情感劳动🤷🏻♂️。她认为体力劳动与情感劳动“存在着为完成工作可能付出的代价的相似性:工作者可能跟习惯于从事工作的自我的那个方面相疏离或异化,无论这个方面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边缘”(霍克希尔德,2020:21)📛。因此,与墙纸工人的身体及其所生产的墙纸不再属于自己一样,空乘人员也与她从事情感劳动的那部分自我相疏离,“她可能会觉得她在这愉快的一天中的微笑并不是她自己的微笑💆🏽♂️,而是公司微笑的间接延伸”(Hochschild, 1989:440-441)🧑🏿🏭。
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家一样,霍氏也同样依赖于一个理想化的外部来激发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手工业生产建构为理想的劳动形式不同,霍氏依赖于私人/公共🆙👨🏽🦲、真实自我/虚假自我的道德二分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所建构的是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对立,那么霍氏建构的则是本真性和非本真性之间的对立🍄🟫💙:她把私人自我等于“真实自我”,她要捍卫真实的和私人的情感生活免遭大公司的入侵(也即捍卫“未被整饰的心灵”),从而维持情感和自我的本真性(Wouters,1989)。因此🎦,霍氏(2020:22👩👩👦👦、35-36、188🧣、222)的批判重点就是私人情感被大型组织出于营利目的而进行程式化🥀、标准化控制时🚣🏻♀️,工人所付出的“人性代价”:自我的健康完整感被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们必须接受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之间的分工和张力。
三、后工业社会的劳动类型与生命政治🐋:哈特与奈格里的情感劳动理论
(一)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范式及其解放潜能🧝🏿♂️: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关怀
哈特和奈格里(2008:274-275)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后现代化转换。在这一阶段,生产知识、信息、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等非物质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开始取代工业劳动,获得霸权地位🤽🏼。而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虽然有模糊性的弱点👏🏼🪮,但“更能说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Hardt & Negri,2004:108-109🙍🏼;哈特♧、奈格里👩🏻🔧,2008:282)。因此👨👧👧,“非物质劳动”的第一重理论关怀,就是从劳动范式重构的角度分析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非物质劳动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智力或语言的劳动,主要生产思想☞、符号、代码、文字等产品👩⚕️;另一种是情感劳动(AL),它是通过实际或虚拟的人际接触🍜,“产生或操纵情感的劳动,如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感或激情”(Hardt & Negri,2004:108)。通过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他们将情感、信息以及知识等看作在后工业生产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要素,并界定了后工业经济的劳动范式:所有劳动和生产都必须接受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也即必须情感化🏋🏽♂️、信息化💍🏊、智能化和交往化(哈特、奈格里,2008)。
正如上文所述🧑🏼🍳,非物质劳动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只是因为“更能说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被坚持使用。而他们更为认同的界定方式其实是“把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也即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最终生产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可能会更好一些”(Hardt & Negri,2004:108)📟。而术语选择的“纠结”,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概念上所寄托的双重理论关怀:既要说明经济转型的普遍趋势,又要澄清这种劳动范式对政治主体的建构作用及其解放潜能(唐正东𓀕,2013;刘怀玉、陈培永🕎,2009)🏇🏽👩🏼🔬。
AL 之所以能为解放提供可能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不再有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再生产劳动的区别,因此从事家务、照料等情感劳动(再生产劳动)的女性与从事工业生产的男性同样属于反抗主体的范畴,在无产阶级的构成中,情感劳动者甚至占据核心位置(哈特、奈格里🈲,2008:58)。第二,对于这一扩大了的无产阶级而言,他们所从事的情感劳动和智力劳动在具体劳动方面的异质性大为缩小,而均质化的劳动过程直接创造了劳动人民之间的共同性🤦🏻♂️,为全球化时代的革命主体“诸众”(multitude)奠定了基础(Hardt & Negri,2004:114)。
(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女性主义🐠: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资源
在为《情动转向》所撰写的前言中,哈特明确指出了AL 的理论资源🕵🏻♀️:“流派一是基于美国女性主义者的工作🏉,他们发展了以情感为核心的性别化劳动形式,如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照护、亲属工作或母性工作……流派二主要涉及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学家与劳工尊龙凯时AG家的著作⟹。”(Hardt, 2007:xi)
1.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对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有一个被称为“机器论片段”(fragmenton machine)的“圣经式”文本。其中🧑🚀,马克思指出,在自动的机器体系出现后,工人的直接劳动在资本增殖中的作用开始让位于体现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机器体系(马克思💂🏿、恩格斯,1998:102)☪️。维尔诺(Virno)👩🏿💻、拉扎拉托(Lazzarato)和皮帕尔诺(Piperno)等自治主义思想家们通过对“机器论片段”及其中的“一般智力”问题的创造性解读👱🏻♂️,提出“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用以说明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模式以及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化(张历君⬅️,2006:153-187)。拉扎拉托(2006:139)最早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生产商品的“文化内容”与(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这两类活动已经从“资产阶级及其后代的特权领域”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成为普遍的“大众智能”。他将这两类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新形式工作称为“非物质劳动”🛻,并赋予其“理解今天的工作及其所暗含的新权力关系”的理论主题。
哈特与奈格里(2008:31-32)明确承认,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指出生产性劳动越来越向非物质化方向靠拢🧑🏻🏫🧙🏼♂️;二是提出了非物质劳动中新主体性的生成及其所具有的革命潜能。但是,他们同时指出,自治主义学者的非物质劳动研究有一个严重缺陷,也即仅仅关注非物质劳动的智力和非实体方面,忽略了作为其绝对核心的情感向度。因此☀️,他们提出了非物质劳动“2.0 版本”,在自治主义者所强调的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和认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n)之外✍🏽,将主要由相对低薪💇🏼♀️、低社会地位的女工承担的情感劳动也纳入其中(Camfield, 2007)。而他们对情感劳动的重视🥮,则与女性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
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在上一小节的讨论中🧻,有一个未及展开的论题,也即他们以什么为标准来判定自治主义者忽略了非物质劳动的情感维度是一种“严重缺陷”。如果把视野放宽至他们在《帝国》中的整体论证思路🙇♀️,就可以找到答案,也可以发现为什么AL 需要在自治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纳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要素🕵🏽♂️。
在“帝国”理论体系中🚶♂️,生命政治具有核心地位(张历君🧏🏻,2006:154),同时,他们还指出对生命权力的分析必须集中在生产维度之上🖖🏽。而在通过福柯和德勒兹的理论资源构造自身理论工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福柯“未能抓住的正是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而德勒兹和瓜塔里虽然发现了生命权力的生产能力,但分析并不深入,只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更好地把握了社会生产和生命权力的关系,但如上所述🏋️♂️,他们也忽略了“情感的价值”。如此,在这一拉长的论述链条中,尊龙凯时娱乐可以看到,情感劳动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生产性”(哈特、奈格里✋🏼,2008:28-32)。
哈特与奈格里(2008:32)认为,要想补救自治主义者因忽略情感劳动而导致的“只是挠了挠生命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就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后者关注的正是“女性工作𓀉、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在物质生产范式仍占主导的20 世纪60 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英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对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性进行了探讨,意图扩大生产性劳动和剥削概念的范围。其典型代表就是“家务计酬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科斯特和詹姆斯认为,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尤其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根本而言是生产性的工作🕕,而其生产性不仅仅体现为这种工作是“有用的”,更体现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创造剩余价值”(童,2002:157)🐇。霍克希尔德(2020:201-204)则指出女性所从事的情感工作和家务劳动一样,都属于不被看见的“影子劳动”。但是她对空姐的研究表明,这种“影子劳动”对公司的盈利具有直接的价值🤿,而且将成为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哈特🦇、奈格里(2016:101)的AL 则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劳动观念更为激进的版本。在他们看来,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重心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
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而且生产与再生产也日益混同”,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工厂中的工资劳动,而是与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相融合。在此意义上👨🏻🦯,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必须被承认为是生产性的——生产“必须泛指人类的创造能力”🪑,包括“对情感的操纵”(Whitney, 2017)。同时,正如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并不直接体现为生产某种具体的劳动产品,情感劳动的生产性也更多体现为一种生命政治生产,“情感劳动生产的是社会网络、共同体形式、生命权力”(Hardt, 1999)。
四🫰🏻、现状与未来:情动转向与情感劳动
(一)情感劳动研究的现状:AL 与EL 的重叠与混用
根据霍氏(Hochschild, 1979🗳;霍克希尔德🥘,2020:21)的界定,EL 至少包含以下元素:发生在雇员与顾客之间、公司或组织对感受规则的界定、(雇员)管理自己的情感、(雇员)展演自己的情感、使他人(顾客)产生某种感受、(雇员)获得经济报酬。但是当这一概念开始被不同学科使用时🧥,其界定就开始伸缩。例如,有的研究将EL 从服务部门扩展到所有的互动性工作,也即将家庭内部的关怀和照顾等不涉及直接经济报酬的劳动也纳入其中(Wharton, 2009);有的研究不再将EL 限定为发生在雇员与顾客之间,而是认为组织内部的同事之间乃至管理人员也都需要从事情感劳动(Steinberg & Figart, 1999;Brotheridge & Grandey,2002)🟰。其结果就是EL 概念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经验现象被纳入EL 的框架之下。
如果说EL 的经验指涉的不断扩展源于不同学科研究者在霍氏清晰定义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对概念的要素进行排列组合或添加😧,那么AL 似乎没有界限的概念范围则源于哈特与奈格里过于宽泛的定义。根据他们的界定,AL 是一种在质的方面取得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后工业社会的所有劳动形式都必须情感化,“在此意义上,AL是每一种工作形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再)生产形式”(Federici,2012:122)。换言之🦦✔️,只要劳动涉及“生产和操纵情感”,都可以被称为AL,只是“这里仍然不清楚‘情感’如何被概念化,以及由谁并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和消费”(Fortunai, 2007:147)🕉。根据奥克萨拉(Oksala, 2016)的分类👨🏼🔧📙,AL 主要包括四种🍂:一是指没有商品化的照护工作,例如养育孩子🙎🏿、照顾生病或年老的家庭成员😹;二是商品化的照护工作或再生产劳动,例如养老院护工🌌、日托中心工人以及最极端的商业化代孕;三是霍克希尔德所界定的EL;四是无偿的EL,虽然个体也通过管理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情感体验🙇🏽♀️,但并不以经济报酬为目的。
而这四类AL 其实都属于扩展之后的EL 的研究范围,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2012 年版)序言中提到了这些类别中的所有劳动形式(霍克希尔德,2020:1-8)。换言之,EL 与AL 所处理的经验现象范围几乎完全重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尊龙凯时娱乐在“引言”中指出的EL 与AL 使用中的含混🧚🏻♂️。
(二)情感劳动研究的未来方向:恢复AL 的情动意涵
事实上👩🏿🍼,情感劳动概念的混用和重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affective labor 中本应具有的“情动”(affect)理论要素在理论建构和后续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阐发🏃🏻➡️。哈特(Hardt, 2007:xi)虽然曾明确指出,他正是运用“情动”的视角来理解AL 在后工业社会的兴起。但是,他们二人在界定AL 时却并未详加阐述,只在《诸众》中简单提及了 emotion 与 affect 的不同(Hardt & Negri,2004:108)🧺。因此✴️🕌,要想真正区分AL 与EL 的适用范围,就必须首先突出哈特与奈格里为AL 设定的“情动”要素🚂,拓展其作为“情动劳动”的一面。
在斯宾诺莎-德勒兹传统中,情动就是身体在与其他身体(物体)发生感触时,身体的存在之力或行动之力所出现的增强-减弱-增强-减弱的连续流变🕎。随着身体感触际遇的变化🥻,情动总是在愉悦-悲苦这两极之间流变🦶🏽,愉悦让身体的行动能力增强,而悲苦则导致身体的行动能力减弱(斯宾诺莎🥓,2016:7-8)。因此🤳🏽♧,情动总是与身体的力量相关联🤾🏽♂️,并且同时融合了身体的行动之力与心灵的思想之力(汪民安,2017)🤚🏽🏂🏿。同时,不同于情感🏭🍦,情动并不是反思性地认知👩👦👳🏻♂️、评估某个情感对象或刺激的结果🙋🏼♀️👍🏻,相反🛣,它是身体对感触中所产生的强度和能量的一种前个体的(prepersonal)体验👨🏻🏭,是非认知👉🏽、非意识的🧜🏻♂️,“带有不可还原的身体性和自发性”(Massumi, 2002:28)。
就此而言🤟🏻,与被社会习俗和文化所结构化的情感相比,情动独立于理性认知,是一种被感触和影响之后的身体潜能,它赋予个体在互动中所产生的无法完全捕捉和表达的感觉经验以强度和力量💇🧺。这种力量使有机体准备对那些正在感触💚、冲击它的东西做出反应,但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方向(而情感及其感受规则预设了个体的行动方向)。换言之“🦹🏼♂️,情动的重要性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信息的接收者来说🧑🧑🧒🚭,有意识接受的信息可能不如她/他与信息
来源非意识的情动/情感共鸣(affective resonance)来得重要”(Shouse,2005)👟🧏♀️。因此,通过恢复和凸显其中的情动意涵,作为情动劳动的AL 可以用来分析这样一种生产与劳动🧑🏻🔧:在其中,劳动者的情感不是被操控的对象,而是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能够在与周围世界的感触中自发地产生劳动的动力与潜能🔳。例如,粉丝无偿的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需要以激发和召唤出粉丝强大的情动/情感力量为前提,同时,随着情动力的迸发和强化,他们不断以高度的能动性进行合作化的集体劳动(如应援🧚🏻♀️、打榜👨👨👧👧、屠广场等)🏌🏼,生成(粉丝)劳动者之间的自动联结💆🏽🙅♂️,而这种自动联结过程中的感触经验又不断激发出他们不受认知控制的情动潜能。再如🏢,Metoo 运动乃至微博热搜等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中,网民们能动地进行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各种文本⛏、视频图像以及愤怒👼🏼、快乐💉、嫉妒等具体感受。而研究发现👷🏽♀️,这种网络事件中“所产生的内容流或新闻流在本质上是情动性的”😮🔫,与公共领域基于理性的协商明显不同(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2012;Papacharissi,2015:4),因此基于情动劳动的视角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新兴的数码劳动。
综上,通过恢复和突出AL 概念中未被详细阐述的“情动”要素,尊龙凯时娱乐可以对经验研究中重叠和混用的情感劳动概念进行初步的区分🐑。第一,AL 适用于强调具有情感/情动的自主性、能动力量和非认知特征的情感劳动类型⁉️📔,在这种劳动中,情感/情动既感染/影响了行动者,又在行动者的劳动中不断被激发和召唤🏢。因此🫄👇,与被社会和商业力量所控制的EL 相比,作为情动劳动的AL 能够摆脱“感受规则”的追捕,在劳动与互动中不断生成创造性🧏🏼♀️⛹🏼♂️、能动性的力量,转变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激发集体行动的潜能。被经常用“乌合之众”来描述的行动者及其活动,如粉丝群体以及参与网络热点事件的网民是情动劳动的最适用对象之一。第二,EL 则仍然应用于经典的情感劳动议题🧑🏿🚀:工作要求(occupational requirements),包括组织机构和工作本身要求劳动者如何管理情感、激励和处罚机制为何;情感展演(emotional display)👨🏼🍼,即可观察到的外在情感表达如何影响目标顾客👡;内心体验(intrapsychic experiences)🪗,人们在工作中整饰情感的内在体验,包括情感与规则之间的失调以及情感与展演之间的失调等(Grandey,Diefendorff & Rupp,2013:5-15)。此类议题通常包含着这样一种预设或前提👸🏻:情感是社会文化规训下认知加工的产物🔀👩🏿🦰,既被个体管理⤴️,也被规则要求,并被资本主义征用✤。第三🏌🏼💁🏼♂️,EL所持有的这种认知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情感观,把情感与认知以及理性锁定在一起,导致其对情感劳动过程中很多深植于身体感触当中、没有固定路线的感觉经验和能动力量缺乏解释的空间。例如❣️,EL 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议题便是EL的消极社会心理后果,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EL的后果并不只有情感失调🧑🏼💻,还可能存在积极体验(Brotheridg et al.,2002🧑🏽💼;胡鹏辉,2018;梅笑,2019)🌦🩳。面对EL框架无法有效解释的这类议题👍🏻,需要走出认知主义和社会决定论的情感观𓀃,纳入情动劳动的视角进行补充,并进行必要的理论整合🎤。
五、结 语
霍克希尔德发现🎅,在“二战”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不仅利用劳动者的体力,而且利用劳动者的私人情感来生产剩余价值👳🏼♀️。米尔斯早就洞悉了这个秘密👱🏿♀️,只是囿于理论工具的不足,他只看到售货小姐需要在大卖场中出售人格。霍氏以戈夫曼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理论工具——情感尊龙凯时AG🛟🚴🏻♀️,以此为脚手架👨🔧,她指出人格市场中的交换关系需要以雇员积极主动的劳动过程为前提——他们必须通过积极管理情感才能生产出在市场中用于交换的人格与感受。因此,随着服务部门的增多🍟🙋♂️,通过唤起或抑制自己的感受让顾客体验到适宜的情感🟣👨❤️💋👨,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大工业时代的体力工人一样,后工业时代的情感劳动者也会与自我及其劳动产品也即情感相疏离⚜️,而自然或自发的情感正是在这个“心灵整饰”的时代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价值。
霍氏是以马克思所描绘的体力劳动作为情感劳动的对话者,侧重于劳动过程,而哈特与奈格里则是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对话🤷🏽♀️,论述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情感劳动🧆🤶,着眼点是劳动产品。基于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研究传统,哈特与奈格里指出🧜🏻,生产信息👤、知识、沟通和情感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在后工业社会取得了霸权地位🦥。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子类别🥣🫄🏿,其研究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工作”也是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哈特与奈格里对情感劳动的进一步阐发,则有赖于从福柯那里借用的生命政治概念。他们指出情感劳动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再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都是生命政治劳动的一部分🪵,或者说,一切劳动都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活,并在此过程中被资本剥削。奈格里🔆、哈特以及霍氏都认为👩🦳,情感劳动带来了新的剥削和异化形式,但是意大利自治主义追求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主体的传统(陈培永,2012),让哈特与奈格里的批判焦点集中于情感劳动所带来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潜能👩⚖️,而非像霍氏一样希望回到“未被整饰的心灵”所代表的本真性状态🚟。
这便是情感劳动的两副“面孔”,它们如此不同,但又如此相像。就未来的研究而言,要尤为注重两个概念的区分与整合。由于EL 概念指涉的经验范围越来越广,而AL 概念本身就缺乏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加之EL 是AL 的概念来源之一,在具体研究中,两者存在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的重叠。面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应该恢复和凸显AL 本身所具有的“情动劳动”内涵,以此为基础划分两者的适用范围👐🏽,并弥补EL 因认知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观而带来的理论局限。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尊龙凯时AG评论》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