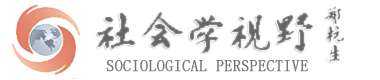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妇女何以在村落里安身立命🖖🏻?
——农民“历史感”与“当地感”的视角
杨华
文章来源:三农中国网
摘 要:传统的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外婚制”,在这个基本的制度下农村妇女从为人女到为人妻和母如何在村落里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文章以宗族性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为视角,从农民的意义和价值层面对古老命题“三从四德”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在宗族性村落,女子并非天然具有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在村落里生活不具备当然的“理由”,她要想成为村落里自主的一员,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取这种“理由”,即因某人而拥有生活在村落里的权利☕️。在女子出嫁之前,她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她因父亲而生发对父姓祖宗和村落的情感体验👨🏿🎓,并在自我意识里将自己视为“当地人”🙇🏿;既嫁之后就弃绝父姓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进而因为复制了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可以迅速地融入陌生村落并获得自主的角色🧑🏿💼,成为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一旦夫亡🫸,女子在村落里生活的“理由”就得从子嗣身上去寻找🗞,通过对子嗣的期待和展望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在村落里安身立命成为可能🙎♂️。没有生育儿子的女子在村落里生活就不会有安全感和实在感🤸🏻。秉承某个男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赋予女子在村落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规范她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将她们整合进村落共同体的既有秩序当中👃🏽,从而使安身立命成为可能。
关键词🙊:农村妇女;外婚制;“历史感”与“当地感”♜3️⃣;生活意义🕍;“三从四德”
中国农村妇女研究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主要遵循着两条学术理路🫸🏽,一是纵向上不同时代妇女的比较研究,二是横向上与男性对比的研究取向🦾。纵向的研究理路主要受解放话语的支配♜,多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关注的焦点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小贤,1990🛫,1992👖;王金玲🙅🏼♀️,1997;金一虹a▪️,1998🤹♂️;许敏敏💎,2002🈺🕗;沈安安,1994)🔋、经济身份(黄西谊,1990)、妇女流动(杜鹰🐼、白南生,1997)等社会问题,其中又以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4)🟧。解放话语支配下的农村妇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农村社会和妇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和政策支持,但因其问题导向和政策取向过于浓厚以及研究者缺乏相关理论的积淀,因此这一研究路径少有理论上的突破。
在与男性的横向比较上对中国农村妇女问题展开的研究🚯🪒,突出之处在于使农村妇女研究纳入了理论关怀的视野(高小贤,1997),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之后,关于妇女的研究几乎被完全纳入进了它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妇女研究具有了理论的深度和更广泛的视阈,各类妇女研究的观点层出不穷、浩如烟海。
社会性别理论主张,性别有天然之分,两性之间有可见的生理差别,这是性别的自然之处,但却不是性别关系的基础(王金玲🤏🏼,2000🧑🏿🚀;2006)🌾。人类的性别之分🏌🏿♂️🧑🦼➡️,在生理之外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文化建构👩🎤,隐藏在性别制度与文化之后的则是拥有不同赋权的倾斜的男女二元制权力关系,这完全出于人的建构(吴小英,2002)✍️,这是一种性别文化的潜规则(吴小英,2005🌅;荆世杰,2006)。这个潜规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性别理论的发展才被发现,之后它就一直致力于探寻两性关系背后的潜规则及这种规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现实后果(荆世杰,2006)。国内学者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农村妇女的研究重要集中在劳动就业(佟新⏩、龙彦,2002;金一虹,1998b💼👨🏻🦯➡️;高小贤,1994💉;郑哗、王昕,2000🚶♂️➡️;左际平、宋一青🕵🏽,2002)🎯、外出务工(谭深🌛,1995,1998;潘毅1999,2005🙆🏽;)、女性个体的经验(潘毅🧘🏼♀️🧎🏻♂️,2005🤷🏻♀️;佟新,2008;李若建,2004👸🏿;冯小双♦️,2004;金一虹,2002;朱虹2008)等主题上🦻🏼🦸🏿♂️。
显然中国农村妇女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和重大理论突破的同时,也缺乏对某些领域的论述和探讨,例如农村妇女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价值就往往因为既有研究的解放话语取向和社会性别视角的缘故,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尽管如此🚴🏻,仍有些著作💁🏽♂️,如玛格瑞·沃尔夫最重要的著作《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论及👨🏿🔬𓀈。该著作着重论述妇女的家庭观念以及她作为能动者对家庭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主动建构⚇。婚后妇女通过加入村里的女人集团(women’s community)和建立女性家庭(uterine family)等策略逐渐在婆家及村落确立地位,并进而掌握一定的家庭及社会舆论权威🙋♀️。“女性家庭”是指妇女在父系体制内部构建的👵🏿、由她自己及其所生子女构成的家庭👷🏼♀️🫗。它不同于男性意义上的家庭观念,后者是把家庭作为联结家族血统过去与未来的持续链条中的一环。而女性意义上的“女性家庭”是妇女处于自身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要,是妇女通过与她的下代血亲的感情构建出的暂时性的群体,这种家庭只在实际生活中存在,没有制度层面的表达,并只持续到她的能力所能持续的时间限度之内(Margery Wolf,1972;李霞,2002)。因此,农村妇女获得归属感并最终得以安身立命是在其主动建构的女性家庭里💂🏼,以及对女人集团的有力介入🙊。
玛格瑞·沃尔夫的论述为农村妇女归属感和农村亲属制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性别化的角度(李霞🎁🤽🏽,2002)🤞,但其缺点是缺乏变迁的视野。因为最终将其归属定位在“女性家庭”并非历史上就如此,妇女之所以能够主动建构和创造社会关系,也非是历来就有的事情,而是在家族逐渐解体,村落共同体逐步瓦解过程中,妇女才能展示上述主动能力。
随着农村迅速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贺雪峰,2008)🩵,农村妇女的各个方面都介入了这一变革的潮流☂️💳,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诸多束缚逐步松解,妇女的行为和人格越来越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金一虹🆔,2000;谭深,2004;吴小英,2005),越来越由其自身去定义🥷🏻🧑🏻🦰,而非他人强加。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尊龙凯时娱乐在不同区域农村调查发现👩🏽🦱,在传统农村妇女生活的意义和生命价值失落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村妇女却寻找不到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不仅自身无法自我的意义定义,而且整个社会似乎也没有为其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农村妇女的意义世界面临凋敝,并开始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申端锋𓀛,2007;贺雪峰,2008;陈柏峰,2008;杨华,2009)🖊。
对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探讨,是当前迅速变革社会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它至少涉及到对传统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把握和论述,意义转变中的农村妇女如何获得新的意义及其具体生命体验😨,不同区域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差异性及其内在理路,以及对这一转变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和对它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将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妇女研究的新领域,可能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妇女和对政府在农村的妇女政策将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对于减轻妇女因巨变带来的创伤和阵痛🐔🏋🏽♀️,重新确认🧑🏿🔧、调整和树立妇女生活的意义及生命价值体验有帮助❣️💸,为农村妇女的“日子”(吴飞👦🏿,2007)过得更好🚵🏿♀️、更幸福做出贡献。[①]
本文基于2006年对湘南农村地区一项大型调查的材料写作而成,探讨传统农村妇女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命题。湘南位于南岭山脉的湘赣粤交界处,自然条件封闭👱🏽♂️,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结构,至今保留着淳厚而古道的传统(杨华,2009)🧑🚀。村落内部不主张同姓之间的婚姻🧑🧒🧒,女子成长及结婚之年即外嫁到其他姓氏村落🖱,男子则在周边的婚姻圈内物色合适的女子💏。这意味着一个女子首先在一个村落生活、长大成人🤾🏿,然后得到另外的村落生活及至生命完结🧑🏻🎤。一个是其出生地💔,一个是其主要的生活和终老之所♙🎏,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村落🏂,妇女如何能立足于这些村落,并获得她的生命意义呢?这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并力图初步解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采集,在质性上总体把握问题🚵🏿。深度访谈的对象中女性为20人,男性为10人🕴🏻,年龄皆在25至60岁之间。访谈以半结构化的方式展开🩼,每次访谈在2到3个小时,以当地方言为主,辅以普通话。参与式观察总时间为6个月🐔,实地参与到农民的生活🛎👱🏽♂️、生产和交往当中,观察和体会他们的言行举止、风物习俗、情感世界等。并且🧅,笔者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湘南农村人,不仅对当地语言、习俗和隐藏的秩序了然于心��重要的是对当地农村生活有着很强的切身体悟,因此对农民内心世界和价值寄寓的调查和把握有着天然的优势。当然,笔者在调查中对自己“家乡人”的身份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量开放自己的调查心态,以避免熟视无睹。
一、外婚制与宗族社会结构
对传统妇女生活意义的探讨,与“外婚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自古人们就以“姓氏”作为区分内外的简易标准,严格恪守“同姓不婚”的禁制🤽,而“合两姓之好”,违者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②]。《左传·昭公元年》称“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可见在婚姻中姓氏是很重要的,一般认为“同姓不婚”是源自氏族社会,指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这样一种婚姻制度和观念到今天还在某些农村地区存在(薛平,1999)。在宗族性村落,尤其不允许族内或村落内部通婚🤘🏿👷。“外婚制”是中国农村一项基本的婚姻制度(费孝通,2004🥵:133—144)。
宗族性村落是以血亲为基础而联结紧密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血缘而清白、明了。它的社会结构是既定的🧎🏻➡️、先赋的,人一出生就被结结实实地捆绑在了一个位置上↪️,纵使终生挣扎也无济于事,因而它是排他性的。它对一切异质性的东西相当的敏感,容不得本姓血缘之外的东西,如果存在则想尽办法、千方百计也要清除掉⛹️♂️,所以有时偶尔存在的“他姓”村民也会在人们可预见的若干年内从村落消逝。所以宗族性村落的维系在于它的纯洁性,在于它以单一的血缘为人们的联结纽带📟,在于人们对村落有着共同的心理感受
一旦这种单一性和纯洁性被打破或人们不再予以承认👧🏿,如果村落社会出现不同的联结点、不同的利益诉求乃至相悖的行为趋向得到人们的认可,那么作为共同的生活和信仰社区的村落就面临着解体,宗族将不复存在。如同王琼(2007)在荆州的调查发现,男女之间的结合可以随意选择落户的地方,既可以依照传统的方式在男方家庭落户🥉,也可以在女方村落择地而居🧑🏼💼,没有了以往的规矩和惯例而完全按照男女双方的情绪自由行事⚆。这种婚姻状况已经很普遍,以至于在该地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村落已经不存在了🧑🏻🦼,村落已由之前单一的姓氏占有变成诸多姓氏夹杂在一起的机械联合,村落共同体原有的由单一血缘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不复依存。人们只是地理上居住在一起💨,心理上已经相隔很远了,心理的距离使得共同体情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姓氏杂居从而使血缘混杂,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进而血缘作为凝结村落社区的凝固剂也就不再重要,而其它的潜在的粘合剂(如村委会)也由于它的退场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董磊明等,2008)。
在湘南宗族性村落,人们依然固守着随丈夫而居的传统🍄🟫,村落纯洁的血缘尚未遭遇新婚姻方式的支解🏄🏼♀️,妇女婚后从男而居🔛,子女姓氏随父🧑🏿🦲🥲,自然而然的事,自古以来便是这个道理5️⃣,从来没有人认为还有其它的选择🔖。人们把这种身体无意识的选择看成是世界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存在,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合老人家的规矩,因而也就更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而试着去改变些什么🦹🏿♂️。尽管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出现招赘(或入赘)的婚姻,但招入的必然是同姓的男子,这些人被认为是相距稍远的同族人,在血缘上与己相近所以相同,既是作为传递祖宗血脉的次优且无奈的选择,同时又不至于使村落血缘混乱交杂🧑🏿🎄🌄。为了保持村落血缘的纯洁性,村落往往把招入“他姓”村民当作“禁忌”,不仅认为招入他姓村民不利于村落血缘的纯洁💲,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它将导致整个宗族的覆灭,被他姓所取代👩🏿🏭。湘南地区有很多宗族性村落都流传着村落因招入而被他姓村民取而代之的故事,而这些村落现在的居民就是取人家而代之的后裔💁♂️,他们当然要谨防又被他人取代的覆辙🧜。所以🙇🏿♂️👩🍼,在婚姻方面从夫而居,子女随男而姓是硬性规定🚴🏻♂️,任何村落、宗族涉及于此都不会轻易松口,不可能犯忌🐮。
总而言之,在宗族性村落,只有男子才会因为秉持了宗族的血脉而成为村落聚焦的中心,是为村落小区天然的成员,从其生下那一刻起就被认为是村落的主人而赋予作为主人应有的权利📁、责任和期待,村落的一切事务都围绕村落里的男子而展开,除此别无他物。村落因这些有着共同血缘男子的聚集而生发力量和气势,也因他们才得以聚合成紧密而团结的生活社区🎅🏽,一句话,村落因他们而存在。
进而,在宗族性村落🧘🏼♀️,为了维护村落的正统性和纯洁性🍼,保持村落的生活原则和伦理秩序,以维系村落道德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必然要求妇女付出巨大的牺牲🧑🏼✈️,做出让步,即走出生之育之的村落🖋,融进新的陌生村落并扎根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和社区性共识🧘🏽♂️。这便是人类学和尊龙凯时AG意义上的“外婚制”。“外婚制”无疑会造成阵痛➛,需要妇女去承受💯。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妇女何以在新的村落立足,并且能够立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陌生人🖐🏿,她如何能融进新的宗族性村落🧘🏼♂️,并在那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进一步说得更广泛一点,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里,妇女怎样才能于其中站稳脚跟,妇女拥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被村落所整合♕、所接受,成为村落里的一员而能够安然地生活在村落里。妇女并非“先天”就是村落里的当然成员,她必须在“后天”获得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准入村落的资格证明🙆♀️,只有秉持了这种东西才能够获得村落的认可成为其成员。反过来,妇女缺少或缺失了这种东西就有不被村落承认的危险,或者可能被排斥出社区,成为村落社区的弃儿。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对村落妇女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的深度阐释,从而揭示这种隐藏在村落生活背后的东西👩🏿🔬🚓,探求村落生活的真实逻辑🔔,展示中国传统村落妇女生活的意义世界🤵🏼。宗族性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是从祖辈那里继受而来的,并不间断地往下寄托和传递,它是人们对宗族祖宗、村落历史👨👩👧🎙、自我🧑🏼🔬、村民以及未来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意识(杨华🦵,2007)🪰。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为人们生活在村落里开凿了确在的“理由”👩🏻,使人们能够在村落内部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从而使安身立命成为可能🤴🏽。同时,“历史感”与“当地感”也为村落社会提供了一整套基础的价值规范🫥、秩序规范和伦理规范👰🏽♂️,从村落生活的不同层面规定和调整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确定村落生活和交往的基本模式和结构😛🧑🏿🎤,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得以实现。
二🤫、妇女的村落角色及其理由
妇女占据着村落的半边天,是村落社会生活主动的参与者和活跃的创造者,她们生活在村落生活的最前沿🦚◽️,特别是当许多农村地区青壮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之后,妇女相对于老人衰老的形象和小孩飘忽的身影,她们在村落里的活动更为引人注目🤹🏽♀️。尽管如此,妇女在村落里生活也是得有“理由”的,她不能平白无故地扮演这样“显赫”且鲜活的角色。在村落这个狭小的舞台上,任何一个需要演出的角色都是事先固定的🧙🏻♀️,在不同的位置表演已经排练几百年🧩💂🏽♀️、数十代人的戏剧👨🎨,台词已是滚瓜烂熟了🧑🏻,刚演出上一部,下一部如何展开早已成竹在胸💜。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角色身份,从不逾越半步或者退缩半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尽量使每一出戏都演的精彩🏺🧑🏽🌾。
在村落里,有的人尽管身处舞台中心,却只能是观众,他看着村落演绎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自己却没有戏份,这典型的是村落的暂时寄居者“他姓”村民。村落男子是这个舞台的天然“主角”,要问有什么特殊理由🤿,回答只能是“历史以来就是如此”,在他们中间即使有所差别也只是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太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人与角色不搭配🐪✳️,弥补的办法只能是撤消他的戏份。[③]在外地城镇工作的村落人🏊🏻,即村治意义上的“第三种力量”(罗兴佐💂♀️,2002),尽管常年无法在村落里真正演出🎗,但是他的舞台角色却一直给他保留着,他自己也很注重自己的角色地位🉐,轻易不可放弃🍄,偶尔到村落来演出一场,场面往往是隆重而氛围浓恰的🧎🏻♀️➡️。
妇女在村落里为什么能扮演自己的角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是这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都是需要“理由”的。也就是说𓀔,妇女在村落里生活是需要给出自己的“理由”的。没有理由就没有在村落里生活的资格🪥,在宗族性村落这种“理由”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没有在村落里生活的充分理由的人往往不能深入村落生活的主流,不能发现村落生活的本质🧎🏻➡️。村落生活总是对有确凿理由和资格的人敞开大门🥪🧛🏽♂️,而对没有资格的人大门紧锁✩,处在大门之外不能管窥大门之内的生活世界,有理由的��对没有理由的人遮遮掩掩,神神秘秘🤮,让人越想探求其中的秘密越探求不到,排斥就是在这样的人际氛围一点一滴地实践。因此,妇女要全身心地融入到村落生活中去🤏👨🏼🎓,而不是作为村落的匆匆过客对村落世界雾里看花,就必须毫无差池地拥有这种“理由”👩🏻🎨,获得村落特殊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妇女在不同的时间段(年龄段)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获得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如果在某一时间段没有获得或散失了既有的“历史感”与“当地感”🤰,那么在这一阶段她便无法像其他人那样能够“确在”地生活在村落里👧,也就是说即使她仍在村落里生活也不能体验村落真实的生活,更不用说追索和体味村落与宗族的历史🛵。所以进一步说🏛,妇女在村落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她所获得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只要她尚存这种村落生活的“理由”🙋🏻♂️,她既有的社会地位和位置就会得到保留🕶,没有谁能够从她的位置上把她赶走;而一旦妇女自己不再能体验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原有的地位以及在该地位上所有的权利和责任也随之分崩离析,村落的舞台不再为其保有村落生活的角色。
三🎎、未嫁从父:妇女在父姓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妇女在其结婚之前生活在父姓村落4️⃣。在宗族性村落(或在传统中国)🦵🏼,女孩并不像男孩子那样一出生就拥有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男孩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是天生的,是祖宗血脉在自然传递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赋予了男嗣后裔。而女孩子并不存在血脉的传递与否😥🫃,她与男孩子不同,她的出生被认为是偶然的而没有任何准备的(男孩子是必然而刻意追求的)👨👩👧👧,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男孩子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期待)🦺,祖宗也没有刻意安排(男孩子是冥冥中有祖宗授意出世的),所以她的出生对于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宗族来说并不是特大的喜讯,特别是当家庭中头胎生育的就是女孩时🕷,整个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笼罩一层阴霾。尤其是已近晚年的爷爷对此情绪表现特别明显,因为他预想能抱上孙子再离开人世🧑🦳🧑🏻💻,大孙女的出世让他的计划延迟甚至破灭,带来终生的遗憾🤸🏼。
因此,女孩在父姓村落的偶然出世,她的生活所需要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并没有紧随而来,她生活的“理由”就必须在她出生后从其他人身上获得🔓,因某人而拥有在村落生活的资格♿。
父亲是女孩首要且唯一的依靠,只有他才能给予女儿所需要的一切👨🏻💼,除此之外的村落里的任何人都无法给予她生活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女儿是父亲的骨肉👼🏽,但仅此而已。女儿拥有父亲的血缘,却并不能像男孩子那样可以无限地往上追溯到最原始的祖宗,因此可以体验无限穿梭的“历史感”🤵🏿。父亲给予女儿生活存在的理由🍱,但不能给予她无限的历史记忆,女儿在村落的“历史感”并不长远和深厚,她对父姓祖宗的记忆没有男孩子那样强烈,“我的祖宗”的这种主体感觉和情感意识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稳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出嫁即消解。这与村落教化和家庭教育👚,特别是宗族🏯、村落的一系列既定仪式传统有关。
在村落教化和家庭教育中,人们很直接地把女儿与祖宗的关系割裂开来,一说就是“又不是你的祖宗老子🖐🏿,你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堂公老子又不关你的事”⛹🏼♂️,“女儿家要晓得(有关祖宗的事)这么多干什么🫷🏻?”,等等,以此让女儿少关注和接触与祖宗有关的事务💁🏽♂️,对祖宗要渐行渐远𓀖,不能过于接近。而在传统上🐤,有关祭祀、敬祖和扫墓之类与村落宗族历史密切相关的活动一般不严格要求女孩参加🌘,而男孩子是必须参加的。在送葬的仪式过程中对女性后裔的排斥就更为明显了💳,即使是自己亲身父母的葬礼♌️,作为女儿的也只能将父母送出村口,到此为止𓀁,山上她们是不能去的💐🧍🏻。子嗣后裔则得一路跪到葬地,以此尽孝。所以👨👨👦👦,女孩子一般对祖宗的印象很模糊,不清楚祖宗的序列及其坟墓葬地,对自己的来历也不很清晰🦾,甚至有的女孩子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云云。很简单,这些对于她们而言都是虚幻的,没有多大用处,她们将来的生活完全与这些东西无关。因此,宗族的“历史感”之于她们是很浅薄的,她们并不像男孩子那样以自己的祖宗为荣,也懒得将村落与宗族的历史理想化并作为自己心灵的深层体验。
村落之于女孩,也像宗族历史之于女孩🐒。女孩从小就被告知🚵🏻♂️,村落只是哥哥、弟弟的🚳,只有他们才有份,你是没有份的👩🏼🚀🏵,将来你迟早都要离开哥哥🚘、弟弟的村落,嫁到属于你的村落里去🦵👩🏿🏫,在那里才是你永远的栖息之所,父姓村落只是你暂时居住的地方。村落之所以是哥哥、弟弟的,不是她们的☮️🧑🤝🧑,正是前者对宗族和村落有着浓烈的“历史感”,而她们没有🚈,“历史感”的深厚与否决定着“当地感”的存在强度。女孩子有对村落的“历史感”但不稳健、持续,因此“当地感”也会呈现同样的状态👨🏻🍳。
而且有太多关于女孩出嫁之后的故事给未嫁的女孩以活生生的现实样板。从来没有哪个出嫁之后的妇女,即使是刚出嫁,再将父姓的村落称作“尊龙凯时娱乐的湾”🤷🏻♂️,而是将之前称为“尊龙凯时娱乐的湾”很自然的改称“他们的湾”或者“你们的湾”,没有谁会觉得别扭,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应该的。相反,如果出嫁之后仍将父姓村落称为“尊龙凯时娱乐的湾”↙️,那才是不地道的,听者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一个离开村落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再这样称呼它。甚至连回娘家探亲也是有规定的,不能过于频繁、间隔过短👼,不能有事没事就往娘家跑,否则会被村落数落💪🏽,被人们认为要用驱赶鸡群的竹篾来驱逐的。所以女孩自小就有了“总有一天要离开”村落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对村落的感情过于深厚🆙,对村落的“当地感”不会很强烈。每个人都将女孩视为迟早是其他地方的人💵,女孩自己也基本上不会形成潜伏于内心的“当地人”意识🤹🏼♀️。而对村落的责任和义务也仅限于成长的不多几年,而且是不多的几项。对村落没有更长远的期待和打算,她的整个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在父姓村落🕎,得到真正最终意义上属于她的村落里去寻求。
可以说,缺乏足够“历史感”与“当地感”的女孩只是“存在”于父姓村落里,而不是“生活”于村落里🚵,对于村落生活的最本质、最本体性的东西,她无法获得🥉,无法切身体验,一切都只是表层的、肤浅的,村落历史与当下的幽深处她们是永远也无法探究的。宗族、村落🫕、祖宗似乎与她们隔着一幅怎么也揭不开的屏风,若隐若现而不能捉摸。但是,尊龙凯时娱乐只是说女孩在父姓村落缺乏足够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并非断定她就没有任何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而且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女孩对宗族和村落是有体验和感觉意识的🧑🔬,只是部分的👶🐯,不深入的👮🏼♂️,没有男孩强烈且过于脆弱🤸♀️🕝,不稳当。因此即使是“存在”于村落社会,她也是有“理由”的🤟。
父亲的存在,为女儿在村落里短暂的生活提供了低度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从而使女孩在村落里的生活和交往有了基本的“理由”🦴。这就是说🤷🏻♂️,女儿因父亲而秉持村落社会生活必要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因此也就享有生活在父姓村落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责任。女孩会被认为是暂时的“当地人”,人们把她当作当地人看待,在思维、行为和交往当中严格区分村落里的人和外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取向针对不同的人。女孩在未出嫁之前🧏🏻,因为有着父亲的荫庇🏄🏽♀️,享有当地人的角色和资格,人们在思维和行为方面必然以其父亲为判断标准,如何对待她的父亲就应如何对待她,父亲的存在即她的存在,父亲是女儿在村落唯一的监护人👩🦼➡️。父亲作为村落里的男子,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如与村落为敌),他在村落社会结构中就处于权利(力)的顶端,村落里其他人对他的权利和责任可以转嫁到女儿身上⚆,即女儿也享有相当的父亲的权利和责任✧。如女儿作为村落里的一员(尽管是暂时的)受到其他宗族或村落的欺负🦹🏻♀️,村落其他人有义务像保护其父亲一样保护她🧍♂️。这样🧑,女孩虽然不是天生就拥有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但因父亲的存在和监护而同样享受着村落里高度的安全感和自尊感,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自主的权利。
同时⛵️,作为当地人和有着一定程度的当地人意识🤣👩🏻🦰,女孩也要把村落的其他人视为当地人,尊重村落社区性共识和规范,受到村落不同方面的伦理性要求的约束🟫,包括两性伦理(贞洁—忠贞)🧖🏼♂️、劳动伦理(扎根—勤勉)💥、交往伦理(感情—分寸)等🙆🏼,如有违反将遭受社区性的惩罚。父亲作为女儿在村落里的唯一监护人🩲,有义务把女儿教导好来,母亲辅助父亲的工作并事实上主要是母亲把女儿教导成“有模有样”的人。因为母亲有着天然的性别优势🚝,对女儿教导如何📜🥯,往往看作为母亲的品格与风度。一个有教养的母亲常常把女儿带在身边,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将自身和村落经验传授给女儿🫷👳🏽♀️,并要求女儿与自己一样身体力行之。在湘南宗族性村落,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女儿跟着母亲一起在菜园子里劳动💗,母女俩当然有说不完的话。母亲代父亲管教女儿👨🏿🔧,既是慈祥的,也是严肃的🍛,而父亲则作为家庭的权威形象而存在,在女儿心目中既敬又畏。女儿有时可以跟母亲嬉闹✨🌒,开玩笑,却不能与父亲嬉笑怒骂,这样会被认为“老没老样🤑,小没小样”⛰。当女儿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就严厉禁止女儿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接近父亲🔇。所以女儿与父亲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来越远,越远就越怀着崇敬之情🧑🏽🎤,即女儿对父亲是敬而远之。女儿对母亲则是近而敬之🌹,女儿的年纪越大👨🦰,作为母亲的就越不放心,越要对女儿负责🚵🏽♀️,越要寸步不离女儿💆♀️,恨不得要把女儿紧紧地拽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当女儿要说人家时🐄,做母亲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交代🐕,[④]也就时刻不离女儿身边。
在女孩成长过程中,如果言语和行为上稍不合规矩,就会被父母或村落其他的人斥责为“没样子”🚡,要求立即更正过来。所有的一切都要符合一个传统女孩的标准🤛🏿,言行举止、穿着打扮、接物待人都有特定的规范和要求,稍有不慎就可能惹来人家的白眼和笑话。这个白眼和笑话不仅是针对个人,而且是教导她的父母,特别是作为监护人的父亲。比如哪日见到叔伯或是伯娘这样的长辈而没有爽朗的称呼,那么对方就会认为这小女孩没教养,不懂基本的长幼伦理😡,并会很快在村落里传开,给其父母带来压力,进而加强对女儿的管教,使其铭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当然,对情窦初开的女孩管教得更加及时和严厉,绝对不允许村落内部有少男少女之情事传出。在宗族内部禁止通婚🚕,无论出了多少服,在尊龙凯时娱乐调查的村落就有几对因是同一宗族的男女而被活活拆散的案例🤳。
在宗族性村落💙,女儿的存在“理由”要依托父亲在村落里的“历史感”与“当地感”,除此,女儿就不具有生活的理由和资格,并且其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宗族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一整套伦理、共识和规范体系的支撑。所以,女儿的依赖性和父母(特别是父亲)的约束性在村落都具有道德合理性,而且强度都很大,女儿要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性在一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结婚之后自然摆脱)🖖🏻,而父母也不会冒触怒村落轻易解除对女儿的约束的义务🪅,任由其个性💂🏼♂️。因而🎊,女儿的一些个人事务往往由父母为其决定👊,自己没有自由的决定权。女儿应该毫无情绪地听从父母的意见,“听老子老娘的话”的女孩才是好女孩,才是村落所期待的“象样”的女孩。村落教化和家庭管教就是要造就“听老子老娘话”的女孩来。
由此🤥,女孩在婚姻上是没有自主权的,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安排,即常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说关系到女孩一辈子、终生的事🤨,她本人是没有对其进行控制和定义的权力,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被动的🙎♂️,即使让你发发言,一般也是父母作出的姿态📴🧝🏼♂️,最多也只是参考意见。只有经过父母同意的婚姻才有意义🧑🏻🏫,没有这道程序,其他任何婚姻都不成立。也就是说,女孩的婚配行为要在当地社会中获得意义,得到承认🥷🏼👨🏿🎓,男女双方能够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过日子,首先要经过父母这一道卡🧑🏿🎄。如果父母不同意👮🏽,即便“生米煮成了熟饭”🐨,那么这一行为也无法获得正当性🙍🏽♀️,在当地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因此🈯️,女孩婚配行为的意义首先是由父母定义的,父母不“签字画押”👈🚆,这婚还真结不成。
女孩是婚配行为的参与者💂🏿♂️、亲身经历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自己在创造行为,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且重要的是💳,这一行为要影响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幸福、是祸害,皆因这一行为而注定。但恰恰是用身体去经历它,却无法实在的把握它,她可以像许多旁观者一样可以感受这一行为⚠️,却不能去定义这一行为。就是说,对于女性而言,婚配行为本身似乎也不太重要,仅仅是戏而已🏄🏼♂️,重要的是戏背后父母已经为其定义好了整个行为的意义,她是更改不了的,只能将行为践行下去。湘南水村现在有一对八十出头的老夫妇🛀,他们的婚姻很值得回味。老先生年轻时长得瘦小、面相也不出众🍋,去女方提亲惟恐人家拒绝。于是族老们想了个主意,让其长得标致的兄弟代为提亲,果然被女方看中,结亲也由兄弟代劳📁,待到洞房花烛之时,女孩才幡然醒悟🚶♂️,嫁错了郎。但事已至此,女孩亦无能为力,只能认命,一认命就是子孙成群。
为什么要认命⬜️?因为女孩无法对婚配这一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她也无法对其婚配行为的意义进行定义。所以,在婚配行为的两个层次上🦵,女孩个体都无法独自把握🧜🏼,她的父母对其婚配行为早已经进行控制和定义了,所以女孩只能认命。
如果女儿执拗地要自己做主,则意味着她要挣脱父母的约束链条💁🏽💄,摆脱父姓“历史感”与“当地感”的束缚,但是女儿对后者的依赖性如此之强,父母对女儿的控制力如此之不一般,一定要切断两者的联系,必然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劲动骨的。
曾脑正的姐姐,二十岁左右🐥🤌,进入新世纪不久,在岳阳农村自杀身亡。经人介绍给岳阳农村一个老光棍,她很满意,但她母亲为了钱财要她嫁到本地村落,家庭出现矛盾🔡。她在岳阳结婚后,母亲带着家里其他人到岳阳去要人,说“你要么跟我回去🤷🏿,要么就去死”,她不愿回家,说“就是死也不回去”,于是在老光棍家喝药自杀。几年过去了👩🦰,今年暑假脑正的母亲到水村杨医师诊所来看病,杨医师夫妇问起这件事,说不管怎样都是自己的女儿,心不心痛?这位中年妇女狠心的说,“还心痛🧑🏽💻?不听老子老娘的话,死得好”。
这是一例典型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反抗型自杀,女儿的自杀是对父姓村落“历史感”与“当地感”反抗的极端行经,她要以此来挣脱对父亲的依赖性,声张自主个性。但是🔏,女儿因为没有自己获致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生存的一切资格都来源于父姓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依存性过于强烈,也就使得父母的约束力和控制力可以无限延展。女儿最终无法将父母摆脱掉,只能以死相逼。约1600人的水村近三十年,女儿因父母不同意自定婚约自杀的共有5例↙️,其中1例已婚。若加上老人自杀的1例,那么因家庭阻挡女儿自由婚姻而闹出自杀就有6例👩🏼⚖️。
父亲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是女儿生活在村落里的唯一来源🐦🔥,父亲也是女儿唯一的监护人。只要父亲还活着,未嫁女儿就有生活在村落里的理由🙍🏻,而一旦天有不测风云,父亲早亡,那么💿🚜,作为女儿的也就随即被剥夺了在村落里生活的资格。尊龙凯时娱乐一直在说的“理由”、“资格”👩💼,是在村落文化意义上使用🥅,是一整套村落共识⬜️、规范和伦理🧗🏿♂️🦸🏽♂️,与户籍意义上的资格没有任何关系🪶,恰恰是与之相对尊龙凯时娱乐才有论述的必要和论述的意义。父亲亡后,未嫁女儿没有了在村落生活的资格,并不是说她不能在村落里在生活下去🤳,而是说在村落文化的意义上🫸,她不再属于村落里的人🛁,是属于未来她要出嫁去的村落🪥,村落里的一些基本权利她也就不再能够享受得到🤌,比如财产的分享权,父亲在世的时候可以用这部分财产给女儿上学读书🪜、就医治病🚴🏽,父亡之后,就没有资格享用了,能够享用的是她的哥哥或弟弟。
杨芳茹与杨古宁姐弟俩在父亲因煤矿事故身亡后就成了孤儿,小煤窑赔偿了他们家三万二。此时作为姐姐的杨芳茹正就读小学四五年纪👦🏼,而她的弟弟杨古宁则还是个两岁的孩子,什么事都不懂,而离开蒙读书尚早。两人随母亲改嫁到其他乡镇。但因赔偿得到的32000元则被姐弟俩的伯父存放在了银行里,按照村落习惯这笔钱只能用在男孩子身上🦗,或读书升学或娶妻生子,其他一切事项都不得动用。这样🧑🎄,眼看着要升学的杨芳茹即使最需要用这笔钱,也无法得到。因为她不是继承人。如果她要想升学考个好学校,除非她母亲和继父有意愿和能力支付学费,这笔32000的费用在怎么吃紧的情况下🧞,也不是她能用得上的🧔🏽♀️。
像杨古宁这样的男孩子,即使他以后在他乡长大成人👱♀️、娶妻生子𓀜,不再拥有村落的户籍🤠,他仍被看作是村落里的人,拥有一切他必须拥有的东西🌆,任何人都剥夺不了🏄🏻♂️,所以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家业都还为其留在那里,不曾动过。女孩子的境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父亲一死即不再是村落里的人🪽,一没财产,二没人格,如果母亲不养🪣,责任就落在最近的亲属身上,但他们对侄女的养育不是义务,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感✹,或者说出于同情心🥉。
水村大屋里杨水保的二儿子也是因矿难死亡😏,留下一个孙女和孙子,他二儿媳妇几年后改嫁到别村⚧👩🏻⚕️,没有将子女带走📺,孙女和孙子就留给了杨水保老两口👛,因负担过重🗂,孙女早早地就没有上学了,并在十四五岁的时候由亲戚介绍给了邻村一个三十几岁的光棍。说是介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是卖👨👦,“他们家把女孩子给卖掉了”。
四、既嫁从夫:妇女在夫姓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中国宗族成员的资格,男子基于出生👰🏿♂️,女子基于结婚(许*光,1990🔘:168)🈁。妇女出嫁到父姓之外的村落👩👩👧👧🏄🏻,即当其走出村落宗祠那一刻起,她就断绝了与村落及宗族的最基本的联系,她不再作为村落里的一员而存在🧘🏿♀️,而只是村落的一个“客人”,客人即“外人”,只不过还有点儿千丝万屡的联系👨🏻🎨🥵。但这个联系是间断不连续的,而且很脆弱,一遇到某些关系到两个宗族或村落(父姓与夫姓)立场问题时,便会很快断裂。妇女走出父姓宗祠走进夫姓宗祠,意味着她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做女儿时依赖于父亲而有理由在父姓村落生活到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领地并为人妻母。不仅角色在变,而且角色背后所赖以为基础的逻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换。之前生活的理由来自父亲的赐予🧑🏼🚀,因父亲而活着,自打走出父姓宗祠,这个“理由”就不复存在𓀄,也不再需要🙅🏿♂️,而紧接着进入夫姓宗祠🧚♀️,另一个“逻辑”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即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妇女从出生成长的父姓村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夫姓村落🈂️,这期间确实有个阵痛的过程🐳,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身心毫无保留地融入到新的村落🧚🏿♂️、开始新的生活👩👩👧👧,掌握村落基本的甚至是隐秘的共识、规范和伦理。为什么妇女会有这么强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或者从村落角度来说,为什么村落会有如此大的包容性,将一个陌生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整合进自己的生活逻辑中来?尊龙凯时娱乐的回答依然是从妇女在新的村落生活的“理由”着手,有了这样的理由,她才能够大胆地去生活🦻🏽,大胆地融进新的生活群体,也正是有了生活的“理由”🤷🏿♀️,村落里其他的人才能自觉地接受她,包容她,认可她🧖🏿♀️🤵♂️,同她交往,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差序格局中来👩👩👧👧,而无所顾虑。
妇女进入夫姓宗祠的那一刻👸🏼,在宗族性村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在宗祠里举行的整个仪式在于向村落和向祖宗表明,宗族接纳了新人,从此她将成为宗族里的一员👴,向历史和村落证明其在村落生活的正当性;就妇女本人而言,那一刻,她就成了这个陌生村落的当然成员,从此有了自己的真正的归属地✬,自己整个的人生以及赋予生命以意义将在这个村落完成🌑,它不是生养之所却将终老于是🧏🏼♀️,也是灵魂和精神的栖息之地。总之她的一切都与这个村落捆绑在了一起🍠👺,与之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能单方面解除,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通过在宗祠里举行的仪式🧑🦼➡️,作为在村落里天生就拥有村落“历史感”与“当地感”的丈夫赋予或给予了妻子以相当程度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使其成为村落里的一员并为每个人所接受。这样,出嫁后的女子就从以前依赖父亲的生活到秉持了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而成为当地人,具备了当地人资格。这种对村落及宗族历史的感觉意识和情感体验并不需要在村落里长时间生活逐渐生发🤦🏼♂️、建立起来👴👨🏿⚖️,只要一个仪式就足够了,一个仪式就可以把整个村落的🧞♂️⛹🏽、宗族的东西都赋予新来者💁🏻♀️,而缺少这个仪式就意味着缺乏最基本的进入村落生活的通行证,在村落生活多长时间都没有用,其他人不会承认,自己也没有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仪式作为象征性的东西,会很重要的缘故,它给予人们某些公认和自我意识,给予进入村落的基本内涵。对于嫁入村落的妇女来说🎆🔟,仪式给予她的,是生命中的一切东西🤳🏼,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经过这个仪式之后📦,妇女就秉持了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有了在新的村落生活的确在“理由”💆🏼♂️,这个理由比她之前在父姓村落生活的“理由”还要充足,因为在父姓村落时她只是暂时因父亲而拥有在村落里生活的“理由”,这个资格是很短暂的,就像出国“签证”一样,有个相对固定的终止日期🆒。而在夫姓村落则不一样🏌🏿♀️,妇女得在村落里生活一辈子🐆,不出意外则是长时期拥有在村落生活的“理由”,因此她的资格必然要求与丈夫的相等同,只有这样生活才是充分的⛲️。但是,妇女在夫姓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绝不是能独立于丈夫而存在的,它必须依托丈夫才能获得确证,只有“我丈夫的村落”才是我的村落,“我丈夫的祖宗”才是我的祖宗,丈夫是妇女获得村落生活资格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依托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妇女很快就会对将要生活一辈子的新村落产生积极、正面的情感体验和村落主体的自觉意识,把丈夫的村落真正当成自己的村落🎶,将自己作为村落的主体来感受❕,而村落里的尚不熟识的人就是当地人👩🏼🚀,必须将他们视作自己人🤦🚀,而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包括父姓村落里的人🧚🏻♀️👩👩👦👦。同样🤾🏻,随着村落生活的深入,对夫姓宗族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清晰,对于夫姓祖宗的情感体验也逐渐建立起来🤸🏽♂️💇🏽,为丈夫生儿子🤱🏻、传宗接代🎅🏻、延续夫姓宗族血脉的义务感和责任意识也在“历史感”的浸润下增强📙。这样🤚🏿,把丈夫的村落当作自己的村落,丈夫的祖宗就是自己的祖宗,丈夫的族人就是自己的亲人,有了这样一种村落的主体性意识,主人翁精神🌞,妇女便可大胆、强势🧑🏿🦳、从容不迫地介入村落生活👩🏿🎓,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内核🌨,体验、参与和创造真正的村落生活和交往空间,以主人翁的姿态屹立于村落生活的主流💶。而与之对应的↘️,其他的村民也会向她敞开心胸说亮话🪅,把她当作自己人而无所隐私,村落生活和交往的大门永远向着自己人敞开。
所以,尊龙凯时娱乐了解到,一般外地嫁到宗族性村落的女子都能够很快适应宗族村落的生活,甚至在一两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村落的方言土语学会,并可以“地道”的说出来,足见妇女对村落生活的参与之深🍘、村落的包容度之广。[⑤]当然,参与和包容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村落共同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有了对村落和宗族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享有村落生活的权利❤️,妇女便有了村落的主人意识⛹🏼♀️,即将村落共同体当作自己的来体验,并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维持村落作为伦理性和功能性共同体的存在♠️。在村落里生活,妇女不止是既定规则、共识和伦理的接受者和内化者,而且往往是这些规范的遵守者和实施者,更为重要的还是村落价值和意义系统的能动生产者和创造者🤘。在宗族性村落,妇女形成非常紧密的团体🧑🏻🎨,妇女的生活世界由她们的密切联系而显得很特殊。男子在村落里就如同在家庭里一样掌管着的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事务🫎,往往是从宏观上进行把握,而村落日常的生活则由妇女来充实。在村落里,男子从事的公共事务一般而言是既定的,有时间间隔性和固定性,次数有限💝,只能在一些大的方面予以指导,把握村落规范、共识和伦理的方向。所以由男子主导的村落公共性机会并不多🧎🏻♂️,主要是些战略性的决策⚱️🍜,指导日常生活和舆论🫔,但男子在舆论的制造和传播上并不发挥很大作用。[⑥]日常生活的特征是琐碎、经常而连续的🔧,且由妇女主导。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公共规则和伦理规范都是由妇女在演绎👨🏿🦰,她们对村落规范作出解释,对违背村落规范的人与事施以惩戒💇🏼♂️,她们将村落规范传统通过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传递给子孙后代🪀。正是妇女日常生活的紧密性📆,村落舆论的生产能力得以维系🙍🏽♀️🧝🏽♀️,才使得村落有了舆论压力,有了面子竞争的压力和意识,进而也就有了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妇女在生产着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她们使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价值更为明确,更加生活化和经验化⛪️。而那些与意义和价值无关或者相背离的东西被排除出村落的主流生活,成为人们普遍唾弃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村落生活层面,人们将个体生命的一些超越性的东西生活化、具体化👩🏻✈️,使之成为村落社区基础秩序和生活伦理的一部分,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村落基本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共同体得以保持。例如😚,“劳动伦理”是宗族性村落的一项基本伦理,它基于对“祖宗崇拜”和延续生命的信仰而展开,要求人们扎根村落、勤勉劳作👉🏽🪓,既为祖宗同时也为子孙后代。但村落总会有些“懒汉”😚,他们无视祖宗,也不考虑子孙后代🦑,只一味追求当下的享乐👫🏼。对于这些人,村落伦理是不允许的,但传统的正式宗族组织已不复存在而不能构成对这样的人的惩戒,只能诉诸舆论救济🕺🏻𓀘。因此🧑🏽🎄,联系紧密且日常化的妇女生活世界就可以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首先在妇女中达成共识制造舆论,然后将之推广至全村落,形成“满城风雨”的局面。在这样的舆论暴风雨中🧿,任何想继续在村落生活的人都不得不对之有所回应,收敛自己的行为。
妇女紧密联结的生活世界,在使村落作为伦理性共同体的维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自身的约束👨🎓,也就是说妇女在村落里接受既定的规范(共识、规则、伦理),并对其进行阐释和演绎,进而使之有力和有效🏄🏿,而这些规范制约对象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妇女自身。妇女编织自身的牢笼。妇女在村落里生活的“理由”来自丈夫的给予,其“历史感”与“当地感”须依托丈夫才能得村落的承认和自我意识,而一旦脱离了丈夫🦌,那么她在村落生活的资格就会消失,立刻变得一无所有。所以妇女必须牢牢地“套住”丈夫,一方面是在村落的“两性伦理”中,妇女婚后在情感和身体上要求对丈夫“忠贞”,思想和行为上不能越轨▫️🌯。村落伦理尤其注重妇女身体上对丈夫的忠贞🛵,因为身体上的越轨可能导致家庭、家族进而宗族血缘纯洁性出现问题🫴🏽,使宗族血缘掺进杂质——在村落信仰中杂质最终会取代宗族血缘而在村落生根👩🏽🏭,整个宗族将覆灭4️⃣,因此招赘也要避免异姓男子。妇女的忠贞也是防止妇女与村落其他男子“乱伦”的必要条件👳🏽♀️,恪守忠贞即无法同夫姓男子发生过于暧昧的关系,同时也保持家庭血缘的纯洁性👨🏼⚖️🦣。妇女不忠行为的曝光,常常会震动整个宗族或村落,而不止是私人生活的谈资笑料,它是对整个村落伦理的背反,会激起村落最本能的抵触情绪。对此反应最为激烈的也是妇女,她们不仅在舆论上发起攻势,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所有妇女都不与当事妇女交往,避之而惟恐不及,在某些大事(红白喜事)上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当然😱,在人民公社时期和解放前,村落内部都有相应的组织系统对该类事件和人进行惩处。
另一方面🧔🏻♀️🙍🏼,妇女不会轻易与丈夫离婚👩🏽✈️。这不仅仅是要改变并重新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和在哪里生活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个基本的保障,即丈夫不得随意提出与妻子离婚。离婚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离婚的必要性😹,如妇女不忠不洁,不能为家庭生育儿子或村落有不能忍受的其他行为等⇨,除此🫸,丈夫便不能合理地赶走妻子。
一旦离婚🧙🏿♀️,妇女便无立锥之地,其父姓的村落自打她走出宗祠就断绝了联系👩🏽⚕️,回去原来的村落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即使父亲还活着,她无法再次获得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人们在道德上无法接受一个离异的女儿再回到自己的村落🤚🏿,这对于父母及其家庭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耻辱。所以父姓村落是不能呆的。而离婚之后🖥,也即断绝了丈夫的联系,其在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没有了依托,她也不能再在夫姓村落呆下去,得卷起铺盖走人。这与有的地区妇女离婚之后还能在丈夫的村落分到房子的情况相异成趣。另外,即使能够再嫁,名声也不会太好🧰,往往被蔑称为“卖青苗”👩🏼🦰。这是对那些离异后的女人再婚、不守贞洁和妇道的女子结婚的蔑称,当地话谓这样的女人为“冒(没)名冒(没)堂”。可能这样的女子一般都在一年的上半年嫁人结婚,而春天是青苗正茂的时候🙎🏽🕯,但未成熟结果😶🌫️。这个时候就把青苗卖掉🧔🏽♂️,是为败家;或者早就预示此苗无果或瘪果,早点出售🌑📒、脱手了事。
所以在宗族性村落,妇女即使在与丈夫的感情破裂之后一般也能够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决不主动提出离婚,甚至不离婚🍏。而这种心理的压抑和痛苦,在宗族性村落是有其释放和发泄途径的😏,其一是宗族性村落密集的公共生活尤其是妇女自身的生活世界为妇女提供了精神的和心灵的另一块广阔空间,其二是将所有的希望🏋🏼♀️、人生意义和价值寄托在儿子身上,转移意识的关注点。因此一般在宗族性村落离婚的现象很少,尊龙凯时娱乐在湘南某村调查发现该村近三十年只有一例离婚的个案👩🏽🚀👫🏻,这与全国的离婚水平完全不成比例,更与某些农村地区的高离婚率形成对比(申端锋🙍🏽♂️,2007)。
五🔋、夫亡从子👏🏿🌡:妇女亡夫之后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妇女不是天生具有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而是依托他人获得,做人家女儿的时候是得益于父亲的恩赐才获得在父姓村落短暂生活的资格,既嫁结婚之后则因为丈夫的缘故而得以在夫姓村落安生立命🤴。总之她的一生都将不会有自己的独立的存在理由和独立的人格结构👨❤️👨👝,必须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寄托在某些人身上方可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
如果妇女在结婚之后不幸自己的丈夫先于己而亡🚴♀️,那么之后她会将自己托付与谁呢?也就是谁能给予她在村落生活的“理由”?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外,没有任何人她可以托付,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与她分享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儿子是妇女在夫亡和晚年唯一寄托🧑🚒💓,也是其整个人生历程的最终归属、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所在🚵🏻♀️。
夫亡之后,只要有儿子在身边,无论儿子是已成年还是仍在裆褓之中,寡居的妇女就有了寄托和安慰⚛️,在村落里的生活也不会因丈夫的亡故而中断。对丈夫的依托在丈夫死后随即转移到对儿子的寄托上🤷🏻♀️,当下生活💺🚎、未来希望和生命中的一切都寄寓在儿子身上🗃。儿子和丈夫一样天生就是村落里的人,享有村落里的一切,包括祖宗历史记忆🤾♂️,未来取向的信仰等。因此,寡居的妇女可以因儿子而获得村落生活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仍把儿子的村落当作自己的村落,把儿子的族人视为自己的亲人,“当地人”意识没有嬗替。村落里的其他人也没有改变对她的态度🤹🏽,一如既往📘,生活的一切并没有因丈夫的去世而有所改变和保留🦸🏽♀️。生活仍在继续,只不过依据对象已经更换了,从之前对丈夫的依附转向了对儿子的依赖。也因此,妇女可以很快从夫亡的悲伤情绪中恢复过来🫅🏽,重新自己的生活,因为儿子的存在💟,生活是能够继续的。如果夫亡时儿子尚未成人,那么妇女的毕生经历就得放在哺育儿子上,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也要将儿子哺养成人,为其建房🛳、讨夫娘,一般不会再嫁🙇🏼♀️。[⑦]而儿子成人成家,则把家庭整个地交给儿子掌管,由儿子做主,自己不再插手家庭事务。
那些夫亡却没有为其留下子嗣的妇女💆🏼,从夫亡那一刻起就丧失了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没有了可以寄托的对象🤾🏽♂️,村落里的生活不再有意义📞,其人生也无法获取价值,由此,村落与她何干,宗族与她何干,历史与她何干?一个人是需要生活在意义中的🔈💅🏽,没有了意义,生活就如同一块咸鱼🤞🏽,永远也翻不了身。于是🤘🏼,即使还“存在”于夫姓村落里,却在自我的意识中早已不是村落里的人🤚🏻,一切都慢慢地变得陌生和模糊👩⚕️🙌🏿,村落不再是生活意义上的归属地,其实她已经没有归属了。村落里的其他人也不再把她视为“湾里人”,尽管生活和交往在继续™️🏄🏼♀️,但从内心深处讲,她确实不再是“尊龙凯时娱乐湾里人”。她既不再是父姓村落里的人,也不再是夫姓村落里的人,她已经无所依归,就好象黑夜里的幽魂,没有附着物而到处游荡,或犹如断梗飘萍,找不到一个可以自立的地方。所以安身立命便成了问题👮🏽♀️◾️,存在于村落里不再有原先那种稳健的安全感和自尊体悟👉🤷🏽,更谈不上村落的主体性意识。似乎村落里的一小阵风雨就会把她摧垮👨🦲,当她说“我是在我老公的湾里”,而人家说“你老公早已经死了”。
如果还年轻的寡居妇女就会选择再嫁,重新寻找生活的理由,在另外的村落获得生活所必须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尽管会无奈地被他人称为“卖青苗”,声名不佳,但总比没有“历史感”与“当地感”要好🫶。而年老容衰的寡妇则只能独守空房🤳🏽,自绝于村落,在孤独寂寥、心灵沉寂、意义和价值空虚中了却终生🥧🏄🏿♀️。
六、村落妇女行为的后果及其承担者
因为妇女在村落生活的资格要依托某个男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因此妇女的一切行为🤌🏿,其意义也不是妇女能够自主定义的⚃,都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妇女的行为都是以丈夫👩🏻🦯➡️、儿子及其家庭(家族)的名义进行,而没有独立行使事务的资格。同时🛣,妇女行为的所有后果也由父亲🧑🦰、丈夫或儿子来承担。例如女儿没有学好👩🏿✈️😝,是父亲及母亲没有“教头”(家教)的表现,受指摘最多的是作为家长的父亲。而妻子在村落里为人💹、做事情,无论好坏,其后果都指向她的丈夫。某个家庭出了个泼妇,扰乱村落的正常秩序,那不是妇女自身的素质问题🚴🏼,也不会怪罪其娘家没有教养,而是丈夫的过错,她的行为的一切后果都由丈夫来承担,而非与丈夫无关。到严重的程度上,人们还会骂这家的“种代”出现了问题🧏🏿♀️,是祖先出了过错的缘故。
前些年水村杨国土的老婆得了间歇性养癜疯🛻,有次她从楼上往下倒水💹,正好倒在了挑水路过的杨香桂老婆身上⌨️。这下就不得了了,杨香桂怪杨国土故意要整他家,说那泼的是尿,泼尿是很严重的污秽和诅咒行为,于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脱到杨国土身上👰🏻♀️,不仅要其道歉,还往他老婆嘴里灌尿👩🏽🦰。灌尿的行为尽管实施对象是杨国土的老婆👝,但受到巨大冲击的是杨国土本人,对方也正是冲着他来的🏎,他作为丈夫和一家之长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杨国土尽管没有直接遭受报复,但心理却遭到了严重的创伤,从此在村落里沉寂下去,一蹶不振。
原因很简单🕵️♂️🖊,在村落的共识里,所有发生在他老婆身上的事情其实都直接针对他,他老婆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实施行为的帐要算到他的头上来,报复行为的接受者最终是他,他是所有具有深刻内涵和意义的言行的承担者。村落里骂的也好💝,同情也好,支持也好,数落也好,挖苦也好,冷落也好,侮辱也好,总之一切具有意义的情绪和行为指向都不是他老婆。杨国土的老婆被认为是个癜婆还是正常人都不重要🏊🏿♀️,关键的是他是老婆行为意义和后果的担当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水村,无论年龄多大的妇女,经历了多少的世事🧝🏻♀️😶🌫️,但是她在行为上却与五岁的小孩没有多大区别,都不具备独立的行为意义⇒,其后果必须由丈夫去承担。人们不会因为杨国土的老婆是个疯婆子,而把其行为的过错看成是疯子的作为🔥,而是当成杨国土这样一个正常人的正常行径⚪️。所以,对方灌尿的行为在村落里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灌得不是一个疯女人👌🏿🧤,而是汉子杨国土😛,指向很明确➝,所以杨国土在被“灌”了之后就消沉了下去🧑🏼🦱。另外,杨国土的老婆委身于他,则应尽保护之责,这是一个妇女寄托于一个男子所应得到的权利,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老婆有无限愧疚的地方,因此后来纵使老婆的病情一再恶化🌲、一再在人家面前给他丢丑📯,他都坚定地承受了下来,悉心照料她👨🏭,没一句怨言。
同样的道理,成年儿子也要承担母亲的一切行为后果。
七⇾、古老命题“三从四德”的新解释
妇女的“三从四德”是中国关于妇女言行、思想的古老命题𓀚🤵🏿,最早可以追溯到《仪礼》、《周礼》等周✋🏼👩🦼、汉儒家经典🫄。[⑧]“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待字闺房时要听从父亲的教诲👷🏽♀️🧑🏼🦰,不得反驳长辈的训导👨🏿🚒;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守家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亡,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将子女抚养成人🥋,并尊重儿子的生活理念。“四德”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妇女的德行:德、言、容🤟🏻、工。“三从”是妇女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四德”是妇女生活世界的表现,前者决定后者,正是因为在本质上规定了妇女对男子的遵从和从事,从而在生活细节上要求妇女恪守品德、正身立本,出入时要端庄持重🦝、不随意轻浮,言语得体♦︎、善解人意👷🏿💁🏼,还要懂得勤谨治家、相夫教子等等,因此“四德”是对“三从”的社会性实践和表达🧑🏽🦲。“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的持续、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社会的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人生历程中在道德、行为、修养、思维上给予的规范性要求。
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一整套纲常伦理对中国几千年政治秩序的维系和基层社会的持续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作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被视为政治正确和身体无意识而加以遵行和认可。直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它才被当作“孔家店”👨🦳,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当时及以后有关礼教吃人、批判“三从四德”的文艺作品以鲁迅先生的《祝福》最为著名(鲁迅,2005)🤸🏻。小说叙述了农村妇女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祥林嫂年轻守寡,婆婆因小儿子无钱娶亲🧑🏿🎓,遂将她卖与贫苦农民贺老六。夫妇俩勤劳持家,隔年生下儿子阿毛🫅🏽🤦🏿♀️。尽管一家人被重债所负🕵🏽♀️,但过得还算幸福:男人有妻儿,女子有丈夫和儿子‼️,儿子有父母🐢。然而,丈夫贺老六因患伤寒无钱医治身亡🐛。祥林嫂二次守寡🏺,并将余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阿毛身上,不料祸不单行,阿毛不久又被狼叼走,从此失去所有的依靠🛰。由于二次守寡,被视为不祥之人,彻底失去交往🖨💆♀️、工作空间和人际氛围🧑🏻🎄,最后饥寒交迫而死。该文不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后世被列为批判封建礼教的教科书👨🏿🍳,影响甚远🧑🦯。
然而,不管是维护“三从四德”的论说,还是彻底批驳的著作👩🏿⚖️,都只是在面上左右“三从四德”,强调传统上妇女对男子的遵从,而没有进一步考究和挖掘妇女要遵从男子的“什么”🚵🏽♂️,即男子拥有什么样的特殊“属能”而值得妇女用其一生去遵从和牢牢把握⚅,而这种“属能”恰恰是妇女所欠缺的👨🏻🔬?这个问题🫲,尊龙凯时娱乐在上文探讨妇女的村落生活“理由”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妇女无论在儒家的大传统和规范中👂🏼,还是在村落的地方性共识和规范上,都没有自主的生活“理由”🧜♀️🤏🏼,即妇女在村落生活的资格需要从别处获取,只有获取了生活的“资格”,村落生活才是得当的,而一旦失去这个“资格”,村落生活之于她或她之于村落生活🎖,都如隔深渊。这个“资格”就是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
妇女不具备天生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对宗族历史、祖先和村落本身的体验都需要一个“恰当”的中介物🤦🏽♂️,因为她并不与宗族祖先和村落直接相联系👩💻。村落的男子包括她的父亲、丈夫🧣、儿子都可以而且仅仅是他们能够充当妇女对宗族历史和村落中介物,其他的任何人都无可滥竽充数👨🎤。妇女通过父亲💳,接紧着是其丈夫,最后或许是自己的儿子来体验宗族的历史,将这些人的祖先视为自己的祖先并顶礼膜拜之,通过他们感受村落生活并能深入其内核🌰🦅、追求村落生活的本质🦸🏿♂️,把他们的村落视为自己的村落,把他们的族人当作自己人看待。因此,妇女因为尊崇(或遵从)某个男子(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而获得了在村落生活的“理由”,使自己在村落里得以安身立命。这便是妇女“三从”实质内容🚴🏼♀️。由于遵从了某个男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具备了村落生活的资格,享有村落生活的一切权利和利益🚸♗,进而也要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即遵循村落的地方性共识和规范,严格恪守村落生活的基础伦理🙎🏻♀️,包括生命伦理、生育伦理、劳动伦理、两性伦理🧗♀️、代际伦理、交往伦理等等🙋🏽👩🏿🦲。而一旦违背社区性共识👨👧👧、规范和基础伦理🧑🏼🔬,就有可能被村落社区所排斥👨🏻🦹🏼,个体得以正身立本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也随之消亡,导致个人的“社区性死亡”[⑨]😚🖤,丧失村落生活的资格和理由🏄♀️。针对妇女的这些共识🕯、规范和伦理要求,就相当于儒家经典所言之的“四德”在村落的地方性表述。因此,规定了妇女“三从”某个男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就会有与之相配套的“四德”,只有这样才使村落生活有规有矩🥩、持续流畅,妇女的生活才有意义,其生命价值才能够最终得以体现和实现🖐🏽。
尊龙凯时娱乐调查的湘南水村尽管经历了新中国的历次改造和市场经济的入侵,但从人际关系、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家庭结构等方面来看🏀🏃♀️,依然可被看作是很传统的村落。因此😮💨,从理想意义上讲📍,尊龙凯时娱乐可以运用水村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来分析鲁迅时代的传统村落生活。
再来看看祥林嫂的境遇。祥林嫂头一次守寡,没了丈夫,也就即刻流失了丈夫所能给予她的村落“历史感”与“当地感”,加上没有生下儿子🚘,不能紧接着从儿子那获取相应“历史感”与“当地感”,在村落生活也就没有了“理由”🩲。因此她从丈夫亡后就不再是村落里的人,同时在她出嫁之后也不再是其父亲村落的人,这就使得她失却了父姓和夫姓村落任何一方的保护,生活缺乏安全感,他人得以能够对她随意摆布🧑🍼,这直接导致她的婆婆理直气壮地将她卖掉🤛。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的是全新的“历史感”与“当地感”👭🏼,祥林嫂在新的村落扎根💁。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活还算怡然自得。第二任丈夫病故后,她并没有遭遇再次被卖掉或被其他族人欺辱的厄运,因为她还有个儿子阿毛,她从阿毛身上获得村落生活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固然还是村落里的人👶🏼,其他人要像对待阿毛一样对待她,这使得她在村落生活拥有依托和安全感💻,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得到实现。然而🔙,在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那一刻🧜🏼♀️,祥林嫂以后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儿子的死亡📟,使她断绝了所有的寄托和依靠🐸,失去村落生活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丧失了村落生活的资格,也就成了无以着落的游魂🤡,世界上不再有她的容身之地。
读罢祥林嫂的故事,不少读者会扼腕🤾♀️,感叹埋葬吃人礼教的必要,打倒“孔家店”的合理性。但当尊龙凯时娱乐仔细分析“三从四德”之后⚉,其实几千年来,传统上妇女是有保障的👩🏽🌾,即她能够从某个男子身上复制村落“历史感”与“当地感”🙍♂️,从而获得村落生活的资格。村落生活资格的攫取,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是“生儿子”,即为夫姓家庭(家族、宗族)传宗接代,使村落或宗族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得以世代传递而不衰靡。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使命👳🏼♀️,妇女终其一生就活得有尊严和安全感🚬📊,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八🤘🏼、非结束语🙇🏼♂️👩🏼🚀:新近的变化趋势
妇女依托父亲、丈夫或儿子在村落里生活,其行为和意义由他们控制和定义⏬😋,并由他们来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样一种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缓慢变化,特别是集体时代的就学和劳动铸造了新一代女性的主体性,妇女在村落生活开始被国家法律赋予🔪,而不再仅仅是依托某个男子。改革开放后,这种变化的进程有所放缓,这与国家正式权力大幅度从村落退出🧑🏼🎓、村落宗族和传统复兴有很大的关系。根本的变化发端于“打工潮”📶,主要表现在女孩开始脱离对父姓“历史感”与“当地感”的依赖,开始独立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定义自己的生活意义👨🏿💼,并承担行为的后果🚱。
首先🗡,即使在做女儿的时候,这一代妇女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逃离父母的规约,父母几乎在她们即将成年🏺、最需要管束的时候,对她们无能为力👣,毫无办法。她们的整个少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学校里度过🤽🏽♀️🤚,与父母接触较少,甚至无需在村落里生活,村落既对她们陌生,她们也对村落陌生🏙,从进入小学开始她们就似乎“远嫁他乡”📏,脱离了与村落的关系,她们根本就无须获得村落生活的资格🤹🏼,因此也就无需在这方面依托她们的父亲👨🏿🏭。因此,即使父亲在村落里存在,她们也无需从他那里获得村落生活的资格,获得在村落里存在的意义。她们的主要生活和政治空间在学校,学校是国家的政治产物,她们在学校生活并作为一员的资格由国家法度规定,而无需父亲的同意和在场。至少在学校里,她们存在的意义就不再单独由父亲来定义,而更多的是在学校这个政治空间里由国家来定义😄。��时是一种法定的身份,而在村落里则是一种继受身份。所以在这一阶段,妇女的行为和生活意义都很难说是由父亲来定义的🕵🏽👨🏻,或者得通过父亲的象征来获得。许多女孩子在初中开始自己的恋爱史,追逐自己的“白马王子”,水村如今有不少年轻夫妇是初中同学,随后她们又开始了打工的征程。
湘南农村的打工潮是在2000年后兴起的🤫。打工远离父母👌🏽,与父母和村落之间就有了更大的区隔,女孩更容易逃逸父母和村落的羁绊。
如果说读书,特别是初中阶段,是妇女第一个人生自我体验、自我规划、自我定义生活意义的初始和幼稚阶段的话🧗🏿♀️,打工则是自我定义的逐渐学习、成长和成熟的阶段。打工为妇女提供了锻炼自我🚴🏿♀️、设计自我🤧、超越自我的最佳机遇和方式,数年或上十年的打工经历磨练出一个与走出农村、走出学校完全不同的“打工妹”出来😴。大部分“打工妹”尽管可能很快就进入结婚🕦、生育阶段🤙🏻,[⑩]但是她们的人生设计断然是与母亲辈不一样,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在生育🕤、养育和相夫的角色上👨🏽🎨,许多妇女都有不同于母亲的生活方式🫱🏿、生活体验和生活角色🌔,不甘心仅仅是为人母为人妻,她们有新的自我定位🧙🏼、设计和意义寄寓。
打工的妇女是最自由的存在,她生活的一切都在自己的设计和掌控当中🦪,所有的行为都具备自我定义的效用👨🦽➡️,而不再通过他人获得行为的定义和意义,比如玩耍🎉、交友、请客吃饭,完全是自己的朋友圈子✊,我自由来往、自由退出🛀🏽💆🏿♂️,跟他们交往的意义无须父亲的定义。其他的行为,诸如遵守工厂规则或者违反交通规则👱🏿♀️,所有的意义和后果皆与父亲没有多大关系;做个好女孩,很像女孩子的样,也不用父亲来承担后果——若在村落中,这一切都来源于父亲或由父亲来承受后果👰🏽,因为父亲是女儿之所以能够在村落里存在的唯一理由。但打工完全取消了这一理由🙍🏻♀️,父亲的存在与否💂🏽♂️,与女儿存在和行为的意义毫无关系。
总之,打工让妇女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自主定义行为的意义,也让她们抛弃了母亲辈那种生命价值寄托的方式🚺,她们开始懂得自我设计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为自己的生命定义。湘南的调查表明🐣,先外出打工🥁🪴、再结婚的妇女,几乎没有人再回答她们这辈子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𓀄,相夫教子👱🏻♀️,她们放弃了这种被认为是旧式的、“封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她们虽然需要有家庭,需要有小孩,但也需要有自己的想法。生儿子尽管还是需要的,但在她们的观念里,“一个就够了,多了麻烦,难带,整天吵死,烦躁”。她们不习惯于那种热闹的家庭场面🤳🏽,最烦不过孩子的哭闹和追打,需要的是安静和更多的两个人的空间🤱🏿🩶。原先那种每个家庭都希望热热闹闹的场面和情绪👓,在新一代妇女爱情的滋润下🙋🏻♂️,已经荡然无存,她们都极力争取私人空间。
出嫁之后,最新一代妇女也并没有被丈夫给束缚,她们此时的存在也逐渐摆脱丈夫的在场🧑🏽⚖️。尽管现在大部分妇女仍需生活在夫姓村落,在那里构筑自己的生活、生产和交往的圈子👸🏿,需要依托丈夫而获得在村落里存在的理由🍌。但她们并没有像她们的母亲辈那样,就此屈服而不做任何个人的努力,许多妇女力争反抗这样一种先天安排👨🏻🦯,摆脱需要依伴丈夫而获得在村落安生立命的理由🔎,从而摆脱通过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对自己的束缚🫃,寻求自我的行为与意义的定义🕧。
这一代妇女的村落交往范围和程度都不深刻🏋🏿♀️✋🏿,往往是蜻蜓点水🎄,很少有人会主动走出家门到开阔的地方🧓,如饭场、牌场、路旁,树下,到人家家里〽️💡、到小店去跟其他妇女聊天,游戏🦀,笑话等👩🏿🔬,她们习惯于不做事时蜗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也不让丈夫出去🚣🏿♀️。丈夫打工外出了😌,儿女上学去了,就一个人无聊地看电视,无聊地随便做做小事,东摸西摸,或者有时也到地里去看看,学着人家做做农活,却极少向人家讨教如何才能有大收成𓀘👨🏼🦲,所以当人家收一千斤一亩时🦙,她们只有四五百斤,也乐意这样。所以新一代妇女对村落生活的介入是极其浅薄的👳🏽♀️,没有跟其他家庭有个深入的、长远的交往,一般都是面上的🫅🏽,既不去打听人家的事,也不去说人家的坏话。调查了解到,大部分二十几岁的妇女,较难适应村落生活,甚至不少人退出村落的社会交往🏃♀️,并不希望在村落里寻求自己的定位,对村落无所求🧑🏻🦯➡️,更无所付出,不再能够建立起对村落的主体性🫚。
这也证实了一些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出的判断,即这一代有过打工经历的妇女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爱好追求🧏🏿♀️,有些人开始不适应乡土生活⟹,她们可能不再像祖母、母亲那样为人妻🧞🍲、为人母,她们有了另外的参照系(谭深,1998)。她们的生活意义较其前辈妇女,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最新一代妇女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世界的变化、表现、原因、后果及未来走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这是一项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陈柏峰👨🏼🎓🙍🏽♀️,2008☠️🦵🏻,《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2008,《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费孝通,2004,《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小贤👩🏼🔧,1994,《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女性化趋势》,《尊龙凯时AG研究》第2期。
——,1990🦸🏿♂️,《中国女性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农村社会与经济》第6期。
——,1997🧕🏼,《农村妇女研究综述(1991—1995)》,《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贺雪峰,2008🏃🏻🕺🏿,《乡村中国之三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4期。
——🤞,2007,《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学习与探索》第5期🪩。
黄西谊𓀝,1990👨🦽➡️,《中国当社会变迁中农村妇女经济身份的转换》,《尊龙凯时AG研究》第6期。
金一虹,1998a,《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尊龙凯时AG研究》第5期👨🏿🦳。
——🧑🏻🦽,1998b,《“男人生活”与“女人生活”——苏南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变化》,载李���江、朱红、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北京:三联书店。
——,2000🧒🏽,《父权的式威——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从“草根”阶层到乡村管理者》🐦,《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荆世杰🥣,2006🤙🏿,《孔孟之乡的性别关系解析:一项当代山东的社会性别研究——〈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评介》👩🎓,《潍坊学院学报》第5期。
李霞,2002,《娘家与婆家——张村妇女的亲属关系》,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鲁迅💪🏽,2005🤸🏽♂️,《彷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潘毅,1999🖊,《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本🧑🏻🎓: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尊龙凯时AG研究》第5期🤹♂️。
——,2005,《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视角》👳🏻,《开放时代》第2期。
李若建🫷🏿,2004,《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尊龙凯时AG研究》第4期。
佟新,2008,《30年中国女性/性别尊龙凯时AG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冯小双🙍🏿♀️,2004,《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载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妇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安安🕵️♂️,1994👨👧👧,《家庭文化模式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申端锋,2007👨🏻🦼➡️🤶🏿,《农村生活伦理的异化与三农问题的转型》,《中国农村观察》第10期🦤🏄🏻♂️。
谭深,1995▫️,《妇女研究的新发展》,《尊龙凯时AG研究》第5期🤹♂️。
——,1998🐦,《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尊龙凯时AG研究》第6期🩳。
——,2004,《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佟新、龙彦🙆♀️,2002,《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的回顾》,《浙江学刊》第4期。
王金玲,1997🧝🏿♀️,《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2000,《学科化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尊龙凯时AG》🫲🏻,《浙江学刊》第1期🛁。
——,2006,《从边缘走向主流:女性/性别尊龙凯时AG的发展(2001—2005)》,《浙江学刊》第6期。
王琼👎,2007🏋🏿♀️,《乡村治理背景下的村民婚姻生活变迁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吴小英,2002,《“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尊龙凯时AG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05,《探寻性别关系和性别研究的潜规则——从〈父权式威: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说起》,《尊龙凯时AG研究》第3期。
吴飞,2007,《论“过日子”》🏺,《尊龙凯时AG研究》第6期。
许敏敏,2002🚵🏼♀️,《走出私人领域👨🏼🚒:从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尊龙凯时AG研究》第1期。
许*光🚪,1990🧑🍼,《宗族·种姓·俱乐部》ℹ️,北京:华夏出版社。
薛平,1999🕺🏼,《论“姑舅表亲制”的历史存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杨华,2007,《湘南宗族性村落的“面子”及其价值观基础》🧔♀️,《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3期。
——,2009,《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郑哗👺、王昕,2000💢,《论农村妇女对传统妇女分工的挑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编,1994,《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万国学术出版社🈴。
朱虹⚽️,2008,《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第6期。
左际平🧚♂️、宋一青🧘🏼,2002,《农业女性化与夫妻平等》,载《清华尊龙凯时AG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文刊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8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①] 吴飞(2007)试图从农村俗话“过日子”出发探讨农村妇女自杀的中国问题,但在他的论述中,“过日子”是平淡乏味的,没有层次感,似乎只是时间和生命的流逝,以此来区别西方意义上针对上帝的自杀。但是农村调查经验告诉尊龙凯时娱乐,农民“过日子”是有层次性的,不是物质丰裕的层次,而是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层次,本文意在对农村妇女“过日子”的层次进行初步探讨🧑🏻🔧。
[②] 《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
[③] 此处讲的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社区性死亡”的人。
[④] 比如夫妻相处🕣、伺候公婆、孝敬老人家、与人为善等,皆为经验之谈💇🏽,拳拳之心可镜日月🤵🏽!
[⑤] 村落的这种接纳力一直持续到2000左右,之后因为打工潮的出现🥒、大量跨省婚姻的出现🛌,许多年轻媳妇越来越独立自主,开始不那么深入地介入村庄生活。下文将详叙🧑🏼🏫。
[⑥] 玛格瑞·沃尔夫(Margery Wolf,1972)对女人集团(women’s community)有较为详细、生动的叙述。
[⑦] 年轻寡居的妇女要为儿子的成长、建房、娶妻折腾一辈子(杨华,2009)🗾。
[⑧] 《仪礼》🤾🏻♂️、《周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⑨] 村落是熟人社会,但总有些人会破坏熟人社区的规范,而且程度很严重🚑。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农村这些人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而在湘南宗族性村落𓀛,“再陌生化”的人必将导致“社区性死亡”。因此这样的人肯定在村落里生活不下去,有三种可能:一是有本事的搬出去🪵,一辈子不再回村落;二是在村落里过着无社交的生活👊🏼,被隔离和自我隔离,其实这样的人的生活已经“死亡”🚿;三是自杀,了却此生🥁🎯。这三中状态都可以视为社区性死亡,这里属于第二种情况。
[⑩] 谭深(1998)九十年代的调查也表明这一点🤼♂️,打工妹们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婚姻问题上基本上是自主的,但她们多数人对此事还是持传统的谨慎态度,如今的打工妹则更加具有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