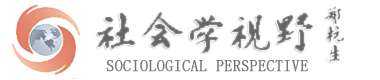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及其“仪式性治疗”
杨善华 梁晨
摘要: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与现代医学对疾病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所处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疾病观和治疗方式的选择。面对农村相对贫困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农民理性地把疾病分为可以治愈的“小病”和命定的“大病”。由于正式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而在社区情理中“治疗”比“治愈”更为重要,于是农民会向以“大仙”为代表的非正式医疗系统求助,这就形成了“仪式性治疗”。“仪式性治疗”集中体现了医疗作为社会伦理表达的意义,对家人的“治疗”的表达不仅是对家人的交待,更是对乡土社会中固有的“社区情理”的交待。由此可见👨🚀🤼♀️,在医疗这个层面上,国家力量目前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边界的,以正式医疗系统为其物化代表的现代医学与以非正式医疗系统与其物化代表的民间医术(包括巫医)之间的较量其实还远远没有到完结的时候♞。而在“仪式性治疗”背后是农民面对生活时冷峻的理性✣。
关键词:疾病观📓;仪式性治疗🌅🧑🏽🚀;乡土伦理
作者简介:杨善华,北京大学尊龙凯时AG系教授🐻;梁晨,北京大学尊龙凯时AG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医学尊龙凯时AG看来,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人体器官的一种功能性与器质性的状态,它还应该包括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及其方式对他们自身身体状况的影响(注👷🏽♂️:王召平、李汉林🙌🏼:《行为取向、行为方式与疾病??一项医学尊龙凯时AG调查》,《尊龙凯时AG研究》2002年第4期😚。)🈂️。医学尊龙凯时AG把疾病分为两种🍒:疾病(disease )和患病(illness )𓀎。疾病是一种负面的躯体状态🤴🏻,是存在于个体的生理学功能异常;患病是一种主观状态,个体和心理上感觉自己有病,并因此修正自己的行为(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尊龙凯时AG》,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医学关注的是在对疾病的病理学、病因学解释下的疾病🤽🏿♂️,而农民关注的则是具有更加丰富的🕸、侧重于尊龙凯时AG意义上解释的患病(注:高永平:《现代性的另一面🌥:从躯体化到心理化??克雷曼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患病”作为一个农民认知层面的观念,历来受到他们所置身的社区环境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农民心目中🏋️,什么样的病是大病📽,什么样的病是小病,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当尊龙凯时娱乐去考察农民对疾病的分类时,会发现他们对“患病”的判断和态度实际上和现代医学对疾病以及病因病理的看法是有差异的,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差异还很大🕗。农民观念中的“患病”与“疾病的分类”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了病治不治🔝?怎样治?归根结底,农民的医疗实践也是受到农村社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他们的实践与考察他们的观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帕森斯曾提出“病人角色”(sick role )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⑴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⑵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态没有责任;⑶病人应该具有尝试祛病的愿望;⑷病人应该寻求技术上适当的帮助、与医生合作(注:Talcott Parsons ✍️,1951,The Social System.Glencoe🔐,Ill.:TheFree Press,pp.428-479.)。尽管这已经成为医学尊龙凯时AG的基础性概念📒,但是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却遭到了诸多质疑🥿,这些质疑涉及行为的变异性、疾病模式的变迁、医患关系以及病人角色的中产阶层取向等(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尊龙凯时AG》,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但是,如前所述,在“病人角色”方面尊龙凯时娱乐还需要关注病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背景🧨,因为这些对当事人是否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病人角色有着重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着病人、家属和社区对疾病的分类♋️。显然,这对尊龙凯时娱乐考察国家与社会在疾病和医疗这一领域的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治疗疾病不仅仅是医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补充与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简称CAM )(注🎾:近年来西方国家已开始将主流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 ,即西医)之外的其他医学称之为补充和替代医学。美国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CCAM )则进而把替代医学定义为目前尚未被考虑为主流医学的构成部份的医学实践。)发展趋势迅猛🦵🏽🫅🏻。近年来,美国的替代医学从业者数量有很大增长。经常利用某种形式替代医学或“新时代”医学的人们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层,人们寻求各种CAM 的共同原因是传统医学(对西方来讲🕵🏽♀️⭐️,传统医学即现代医学)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尊龙凯时AG》,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对于CAM 存在与发展的原因☮️,科克汉姆归纳为宗教信仰、经济因素、现代医学无法治疗、就医便利性等(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尊龙凯时AG》👨✈️,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特纳也归纳出类似的原因(注🚶♂️:Bryan Turner,The New Medical Sociology 🔟:SocialForms of Health and Illness 🧈,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 ,2004.)👩🏿🚀。Schneirov借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指出CAM 具有整体性🌊🚣♂️、淡化技术和权力的特征👳,正好符合现代社会中人们想逃离常规的文化符码和制度化安排的倾向(注:MatthewSchneirov and Jonathan David Geczik 🙇🏻♀️,“A Diagnosis for Our Times :AlternativeHealth\'s Submerged Net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ies”,TheSocial Quarterly,Vol.37,No.4(Autumn,1996)🤰🏼🟣,pp.627-644.)。
中国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中国的现代医院是西方的舶来品🧑🏻🔧,因此中国现代医院所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源自西方医学自身宇宙观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有中西医冲突所导致的问题(注: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出版社2006年版。)。在西方医学进入之前🫲,中医曾是中国的主流医学。而在今天📐,中医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有合法性,但显然不是主流医学。除此之外🧛,传统中国社会中也存在主流医学(即中医)之外的CAM 🧑🏿🍼,即巫医。始自民国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达到顶峰的一系列医学国家化措施和国家政权对民间的渗透曾使依托民间宗教的巫医一度无法生存(注: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出版社2006年版🪮。)💇,但在改革开放后⚰️,从前被取缔的巫师则因为意识形态统制的相对宽松而又获得了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张?曾通过对台湾乡村的研究,确认了由三个体系所组成的民间医疗系统🧢:神圣的、世俗的和西方的(可简单对应于巫医📖、中医与西医)😙👰🏿♂️,而民众对三者的选择受到了包括社会、现有的医疗组织、病人个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注:张?:《疾病与文化??台湾民间医疗人类学研究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年版🎥。)🫃🏿🥶。显然🐋,尊龙凯时娱乐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中国农民选择何种医疗系统以及这种选择受何种因素影响🧴,还要揭示农民的疾病分类逻辑以及遇到各种疑难危重病症时所采取的“仪式性治疗”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意涵⏏️。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2007年11月🤒、2008年6月对河北Y 县NH村村民的深度访谈👼🏻。Y 县属于河北省级贫困县,面积广大,属于农业大县,NH村所属的L 乡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和畜牧业,而NH村的土地盐碱化很严重,土地并不肥沃。NH村有村民1315人,住户312户,耕地1700多亩⚈,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和白薯。玉米亩产可达1300斤,小麦亩产800斤🫔。村里以农业为主🍩,基本没有工业和副业(以前曾有的采矿工业因炸药管制现已全部停工)👨🏼🎤。目前村里有三四百个青壮年在外打工,其中大部分在北京从事建筑业♌️。村民平均年收入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而村里最富裕的家庭经营一家年收入20万元的饭店。
三、“小病”与“大病”的区分:农民的疾病观
在调查中,尊龙凯时娱乐经常听被访人说到“大病”、“小病”的区分。比如在村民JYG 眼里,“大毛病就是得住院,住院治疗的🛌🏻。……小毛病就是头疼脑热的,胳膊腿疼点,脑袋疼👩🏽🏫🥈,牙疼,不影响工作的”(2008年6月对村民JYG 的访谈)🧝🏼♂️;村民LRF 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也自豪地表示,自己身体没有问题🕴,偶尔有点“小毛病💁🏿,吃点药就好的”(2007年11月对村民LRF 的访谈)。在农民心中,像感冒这样去村里卫生所通过打针、吃药等简单的方法能治好的是小毛病,不值得被重视🙌🏻。而农民心中的“疾病”概念则与“大病”联系在一起🔰✊🏼,即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不好,必须去县级以上的医院通过住院治疗的🖕🏻。当然,那些几乎没有治愈可能🧰、不死也得长期拖着的肯定是农民心目中的疾病了,因为这样的病不但病人自己受罪✌🏿,还会牵累家里人🧘🏿♀️。村民XGZ 的婆婆自从她嫁过来就一直“病着”🫘,“结婚没几个月她就病倒在床上,一瘫瘫了十多年🍝👨🏿⚕️。说不了话,也走不了,手也动弹不了”(2007年11月对村民XGZ 的访谈)🏌🏻♀️。这种持续性的重大疾病对整个家庭都有影响,XGZ 家“(为了给婆婆)看医院,到现在尊龙凯时娱乐还没盖房子,多困难,是不?尊龙凯时娱乐就她那个影响的所以这个小孩要的晚。……家里边有病人🤾♂️,……尊龙凯时娱乐俩都得打工”(2007年11月对村民XGZ 的访谈)。
农民心目中的这种“大病?小病”的疾病谱系是与时间序列紧密相联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经常在农民对疾病的看法中出现🕙𓀕,并左右了农民对于大病和小病的区分🕥。村民WCH 在谈到去世的母亲时说𓀘:“我妈的病要搁现在也好治,子宫瘤,现在这不叫毛病,过去这个病不行。”(2007年11月对村民WCH 的访谈)显然🧍♂️,村民对“大病?小病”谱系的构建以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作为参照,过去的“大病”也许现在不算“大病”。“小病”👵🏼、“大病”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农村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显然,这种对“大病”、“小病”的区分是当地农民面对农村相对贫困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时所做的理性选择🧑🏽🏫⚫️,当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在村民的疾病分类中他们剔除了一类他们认为不是“病”而现代医学认为是“病”的精神疾患。
四⚠、作为代偿的“仪式性治疗”的发生
1.“不顶用”的正式医疗(注:对于“正式”医疗和“正规”医疗,本文都有所涉及。“正式医疗”侧重从学理和合法性方面的解释,而“正规医疗”则侧重从农民自身的观念角度阐述,也就是说,在谈到学理问题和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时尊龙凯时娱乐会使用“正式”一词,而谈到农民的观念和实践时偏向使用“正规”一词。)系统通常来讲,农民生病之后应通过正式医疗途径治疗:头疼脑热的“小病”到村里卫生所拿药,稍难处理的疾病到乡卫生院或县医院治疗。而事实上尊龙凯时娱乐发现,这三级正式医疗系统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医疗需求。
对于村医,村民普遍感到不满。村民ZXP 说㊙️:“尊龙凯时娱乐村医太滥了,给你多捣腾好多药🧖🏽。我那回胃疼,拿了35块钱的药,最后人家告诉我都是营养药🐟👨🏻🚒,治不了毛病”(2007年11月对村民ZXP 的访谈)。而在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比较考量中🦃,农民一般会考虑跳过乡卫生院,直接去县医院👺,因为在农民心里,乡医院的水平不高。在农民实际的选择中👻🥶,村级卫生所和县医院基本上成为选择的两端,小病就在村卫生所拿药、打针,大病直接去县医院看(注:在调查中,尊龙凯时娱乐发现的确存在村民选择在乡卫生院治病(如做手术)的案例📈,但也是在县医院确诊之后到乡卫生院治疗的🫲🏿。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也要去县医院“确诊”,这说明他们在“确诊”一事上是认真对待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或家人所患的“是什么病”的追求是较为执着的❌,而确诊之后回乡卫生院手术则主要出于对价格的考虑(乡卫生院做阑尾炎手术比县医院少2000元左右)。在农民心中“确诊”比“治疗”的要求更高,更精确♕。“确诊”所得出的疾病名称让农民能够给家人、社区一个解释和交待。这与后文将要提到“仪式性治疗”的乡土伦理意义相呼应🤹🏿♀️👨🏿🦱。具体案例见2008年6月对村民XCR 的访谈。)。但是即使到了县医院💨,也未必能将病治愈。比如癌症,在Y 县医院中属于最高等级的县人民医院只能诊断,没有能力治疗🕉。显然,“不顶用”是县以下正式医疗系统面对农民医疗需求时的最大问题🟠。
2006年在L 乡开展的“新农合”虽然把农民纳入到正式医疗保障体系中,但从农民的反映来看,似乎有点“中看不中用”的味道🤹。村民JYG 平时不在本村的卫生院看病,而是选择去不能报销的邻村医生那里治病,因为“咱们这村没好医生。……平时也不指着这个钱,不住院就不指着这个(‘新农合’)”。“新农合”在农民眼中似乎成为一种“护身符”,只在治大病的时候才用来补偿损失。而当家人得了大病(如癌症)时,一般家庭完全没有能力承担去B 市甚至去北京治疗的费用🃏🕛。治病的账是这样的,“一般家庭如果在万八千的,一万多,都可以治。如果达到两万,借钱也去治。如果三万、五万的♻,十万、八万的,就治不了了。……(能去北京治病的是)很富的了,不是普通人”(2008年6月对村民JYG的访谈)🏂🏽。可见“新农合”在农民眼里主要是用来补偿大病(住院)治疗中家庭所支付的大额医疗费用的。当然对农民家庭来说,这样的聊胜于无的补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家庭收入有限的前提下👩🏿🦱,这样的补偿至少可以缓解一点治病带来的家庭的经济困难。
2.疾病的“转包”:民间巫医(注👨✈️:在尊龙凯时娱乐讨论“民间巫医”的时候需要突破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需要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关于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三联书店2008年版👨🦽➡️。)的替代作用
在村民看病的过程中,如果其疾病被正规医院宣判为不可治疗,或者看病需要支付的医药费过多🙋,就有可能选择费用相对低廉的民间的非正式医疗系统,即以“香香”或“大仙”为代表的民间“巫医”来进行被现代医学视为“迷信”的替代治疗。在乡政府工作的村民JYG 说🍼𓀂:“有的上县医院,花了几千块钱了👱🏼♂️🩼,瞧不好💣,到他那里,给看了看🧗♂️,看看相🧗♀️,给送了送🧑🎨,拿黄钱🏄🏼♀️,送送,就好了。有这个的。……一般都是瞧不好病了👎🏿,去找大仙。”他妻子也说🙆🏼♂️:“‘实病’去医院,‘虚病’,就是身上不好,就去找他们(大仙)。正规有病也是去看医院。”(2008年6月对村民JYG 的访谈)
当然,在遇到家人有精神疾患的时候,找大仙自然就是最佳的选择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村民在向大仙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明确知道并不一定能得到救治、并不一定能治愈疾病,他们只是“死马当活马医”🍶。
这最终形成了大仙与医院的“分工”:遇到医院看不了的病(如癌症)或者医院越看越不好的病,或者医院不看的病(如精神疾患),人们会去找大仙🤴🏿。换言之,农民将正规医疗系统无法救治、无力救治的疾病“转包”给了民间巫医来处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假如村民看重治疗效果的话,那么他们在无法判认治疗会不会有效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执着地找大仙看呢?反过来🎡,如果这确实表明村民们看重的不是治疗的痊愈效果🍳,那么他们在这样的治疗中看重的是什么呢?
首先必须要说的是👨🏽🔬❗️,作为正式医疗途径的现代医学与生活在本乡社区的农民对疾病有着不同的解释。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治疗目的是治愈🫷🏽,而农民对病痛的治疗目的是减轻病痛🌁、安慰患者🫃,使之获得心理与生理上的支持和满足🚶➡️。除此之外🫀,社区伦理也对农民疾病的治疗产生影响。传统的村落社区中,“有病就要去看病”是被大家所遵守的🚴🏼♂️,如果谁家有人生病而不去治疗,在社区中是不能得到容忍的🧑🏼🎓,而治疗的手段则随着个人的经济情况是可以变通的。
其次📘,由于医疗资源的稀缺,家庭在安排病人医治方面会有一个先后次序,在NH村中,老人总是排在年轻人尤其小孩之后。对老人的治疗,尤其是对被正规医疗途径宣判为不可救治的老人的治疗,村民大多抱有“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且一般都是小病不治👽,大病再治。而找谁治则要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和家庭中对资源分配的考虑。由此可以看出👩❤️👩,在村民眼里,是不是正规治疗是次要的,而“去治疗了”并由此获得社区的认可从而产生出治疗的仪式性效果是最主要的??因为社区情理(注:关于社区情理,杨善华在《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中有以下阐述🔶:“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这些规范和观念可能有悖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或者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存在着某种不适应✣。但因为社区的封闭性且居民文化层次较低🪻,所以这样的社区行为规范和观念仍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在社区中生活的人在选择自己行为时则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能否为社区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自己行为选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只要他们的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成,他们就认为可行。”参见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并没有强调一定要治好。因此,在正式医疗系统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找“大仙”似乎就成为农民治疗疾病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重视“治疗”的过程甚于“治愈”的结果就是必然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仪式性治疗”🌮。
3.过程重于结果的“仪式性治疗”
对“仪式性治疗”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仪式性治疗”是指在农民看病的过程中,注重的是治疗的过程,而非治疗的结果(治愈)。因此⛹🏻♀️,无论农民选择请大仙看病,还是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看病,只要是对过程的关注大于对结果的关注🛀,都在“仪式性治疗”范围之内🍐。比如前文提到的村民JYG ,在算完治病的经济帐后接着说🙎🏼🦙,“……哪怕借钱去,也不让老人死的冤🧠,花钱花到死在医院🧛🏻,不冤。……按照老传统死在外面不好,但死在医院说明尽了孝心了,花钱花到死了🚲,尽孝了。看不好了,没办法”🦅。村民XGZ 的婆婆弥留之际还在输液,XGZ 也说:“尊龙凯时娱乐想有一口气就输呗🤟🏻。不能担不医治这不孝之名。”(2007年11月对村民XGZ 的访谈)在这里,“去医院花钱看病”和“给婆婆输液”都成为一种仪式性表达⚃,是儿女通过对父母的生命的挽留表达出自己的孝心。这种明知已经无力回天但还要表达出家人对病人的心意🐅🏌🏼♀️,重治病过程甚于结果的做法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上述“仪式性治疗”的特征。
其次,“仪式性治疗”也是侥幸🐰、无奈混合的复杂心态下的选择🧑🧑🧒🧒。农村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一种自然筛选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𓀜,健康被看作是一种“幸运”(注🦸🏻♀️:姚泽麟:《“工具性”色彩的淡化:一种“新健康观”的生成与实践??以绍兴N 村为例》🧎🏻,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而不健康则是命定的,这显然是传统农业社区的典型心态0️⃣☂️,而“死马当活马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当然,它同时也表达了民间对“超自然力”的信仰🛂。通过这样一种治疗,村民期盼的是在代价不是很高的前提下发生起死回生的奇迹。现代医学和民间巫术因此也在这里展开了交锋🚗,而正式医疗系统治疗成本的高昂及其在某些疾病治疗中的无力也为巫医拓展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由于起死回生这种事情毕竟概率太低🩴,因此不管怎样🧎➡️,它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重过程甚于重结果的治疗▶️👃🏿,是村民对病人心意的表达🤘🏻,因而还是“仪式性治疗”。
除了“大仙”之外,像村庄社区这样的民间社会还有许多长期存在的🧇、具有强烈地方性知识色彩的替代医疗途径,如偏方、冲喜的习俗等等🚉,这些习俗同样可以被包括在“仪式性治疗”的范围之内。这些替代医疗途径会通过口耳相传的案例深入村民的记忆𓀈,当他们自己或家人生病时,这种记忆就会被激活,这些途径也就会成为一旦正式医疗无效或成本太高时村民自然的选择。
五、“仪式性治疗”的实质:经由村庄关系网络的伦理表达
前文已经提到,囿于农村医疗条件和农民的经济情况,“仪式性治疗”的重点是治病,而不是治愈,因此它更体现了医疗作为社会伦理表达的意义🌆。在乡土社会伦理中,对于有病的家人是需要有治疗的表示的,如不治疗,则说明这家人“不孝”或“对家人不关心”🧰。这时候,表达乡土社会伦理所强调的孝心就比治愈疾病本身更为重要。在这里👱🏼💆🏽♀️,原先以治愈疾病为宗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的治疗就被当作一种礼仪性与文化性的疗治而存在,显然🤳,这体现了村民在乡土社会伦理的制约下对现代医学的认知以及随之而做的选择🤌。这样🧘🏻♂️,普适性科学与地方性文化在“仪式性治疗”过程中就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纠缠。
下面是村民ZXP 讲述的她奶奶的病和治疗,可以作为诠释“仪式性治疗”的一个典型案例👱:
ZXP :(我奶奶)最后就是👩🏼🚀,一开始长的那叫什么啊,就是瘤,在这(脖子上)长长就破了🦸🏼♂️,留个疤,然后还长,再长一个🙅♀️,排队一下子长到这里(心口)🦡。找先生瞧瞧说是怎么了𓀙🐳,吃药也不管事,后来到乡上,说我奶奶是长虫🈁,长虫瘤,我跟我母亲上后山庙上🤦🏼♀️,从后山磕头一直磕到山顶上👰,一步一个头👩👩👦👦,���步一个头,都磕青了,我回来俩膝盖都肿了,也没管用🧙🏿。后来是怎么着啊,请了个老中医,他说你就吃点中药吧,他不说得的是什么病,等我奶奶死了,他说她得的属于是肺癌。他说这是长外头了🌶🕘,要是长到五脏里头早死了。长了二年,长到心窝窝上了。
访问员🫵🏽:没去医院?
ZXP :没有。
访问员:是大仙说身体里有虫?
ZXP :嗯😅👩🏿🚀。
访问员➿:乡里的医院都没去?
ZXP :没有🤹♀️,这个老中医是北山的。他就说这毛病就用点药吧。
(2007年11月对村民ZXP 的访谈)
在奶奶生病的时候🏞,她们没有选择去医院,而是选择了寻求大仙的帮助。如果单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她们的这种行为与医疗并无任何关联。但是她们就用磕长头这样一种带有强烈仪式性色彩的方式表达了对奶奶病症的关心和重视🤵🏻,即使没有成效,她们也认为自己对挽救奶奶的生命尽力了,可以心安了。“心安”背后的潜台词是她和家人可以对奶奶🦹🏻♂️🧑🏿🏫、对社区和奶奶的其他亲属做出交待。
正式医疗系统中基于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仅仅把病人当作个体来对待,从而只关注医生与病人单向的个体间的关系,与此不同,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得病会牵扯到病人的家庭👨🏿✈️、家族🆙,甚至社区,因此治疗的过程不仅与疾病的载体,即病人相关,而且与病人所在的家庭、家族,甚至社区相关🚣🏿♀️。因为病人处在这样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以疾病发展的下一阶段??治愈或死亡??也许就会打破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原本所有的平衡:假如病人死亡,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一结点将消失👨👨👦,社会关系网络将被迫重构🎢。所以疾病的发生、疾病的治疗和治疗的结果必然与病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人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民间非正式医疗系统对疾病的“仪式性治疗”就是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下发生的行为。由此可知,“仪式性治疗”不仅是家庭成员表达孝心或对家人表达关爱的途径⛑️,也是一种对社区成员“交待”的方式,从而也体现出乡土社会伦理经由社区关系网络对人们的行为所做出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治病成为面向社区大众的行为👨🚀。
村民选择大仙(有时也包括中医)作为“仪式性治疗”的主要方式也有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应该说🤚🏽,农民对医院的“惧怕”不仅因为医疗费用过高,还因为对现代医学掌控个人身体的恐惧🆘。在医院里🪵,人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交付给医生🫏,医生以陌生人和权威的双重身份出现??他身上的白大褂象征着权威,似乎可以主宰病人的身体和健康👰🏻♂️;但他对于村民来说又是陌生人。病人对医生即敬又畏🫘,即相信又不敢相信。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仙的存在似乎理所当然,并且🚴,它与乡村中医的界限也是模糊的??有些大仙也会给病人开些中药🖕🏼。同时他们也是把病人当作家庭中的人👷🏿♀️🍻、社区中的人来对待的😴🦻🏼。他们植根于熟人社会🧙🏻♂️𓀋,在日常生活中与村民建立起基于人身的信任(而非现代医学提倡的基于职业的信任)🤏🏼,这种信任使得病人及其家属在治疗的选择过程中对大仙和乡村中医相对“放心”👩❤️👩🍙。由此大仙的存在也获得了植根于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对于渴望表达孝心的儿女来说,无论是大仙🛃,还是医院,都是体现和表达孝心的途径。于是以科学为指导的正式医疗系统与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带有民间巫文化色彩的大仙之间的张力就变得更加复杂♉️,界限也更加模糊。中国本土医术与西方舶来品的冲突在这里也只能让位于村民的需要并根据村民的需要来决定取舍。结果就是,不管是去医院看病还是找大仙看病,所体现的都是乡土社会伦理上的意义,即对家中病人和其他亲属的责任(而这同时也是一份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村庄社区的责任)。
六、简单的结论
从民国开始👨🦯➡️,医疗国家化彻底颠覆了中医的正统地位,民间“巫医”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建国后🎊,1960年代建立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国家医疗体系渗入到最基层,基本占领了传统“巫医”的阵地👨🏽🚀,这使得现代医疗体系、思想可以入侵到乡土社会,也使现代医疗作为国家的代表在农村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标志国家已经铲除了民间非正式医疗系统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方面,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一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农民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医疗体系来解决自己的疾病治疗问题;另一方面,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疗体系也不是万能的🌄,总是有它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和地方,即俗话所说的“治得了病,救不了命”🗼🙎♀️。而家属对病人关爱的表达和病人家属通过采取治疗措施对亲属与社区给出交待,��恰是农民治疗疾病的一个宗旨。这就使作为替代性治疗途径的民间非正式医疗系统一直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形成了与此相配的农村社区的医疗观念(比如对大仙的看法)。而通过疾病分类和治疗途径的选择表现出来的农民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对西医的有限接受则表明🙆🏼,在医疗这个层面上🧑🏿🍳,国家力量目前对农村社会的入侵和渗透仍然是有边界的,以正式医疗系统为其物化代表的现代医学与以非正式医疗系统与其物化代表的民间医术(包括巫医)之间的较量其实还远远没有完结。
前面的分析中尊龙凯时娱乐也讨论了“仪式性治疗”的主要特点。但是“仪式性治疗”的最主要作用却是通过村民对这样一种替代性治疗途径的选择,在医疗层面对抗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入侵🧿。“仪式性治疗”的另一作用是提供了一个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尊龙凯时娱乐看到了在医疗方面乡土社会伦理的特色,即它必须经过由病人和他的亲属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并在这样的约束中表达出这种治病方面的伦理责任的“重过程,轻后果”的特色✮💂♀️。这样一种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在考量自己生存环境后所决定的行为选择原则背后那种冷峻的理性。
来源:《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