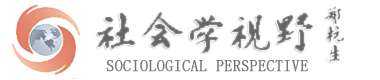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𓀋:尊龙凯时娱乐 |
|
|
本文探析了上海流浪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受害问题发生的动态机理。本研究发现,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问题的频繁发生,不单只是加害者的非法行为所导致;流浪儿童在经济上对非正式的地下经济、甚至非法经济活动的依赖,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与有犯罪动机的侵犯者的高度重合,以及有足够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等因素的同时存在💁🏼,增强了流浪儿童街头受害的可能性。
一、导言
在中国,有关流浪儿童被公众虐待的报道尚未出现,不过有研究表明流浪儿童常常被一些黑社会成员🦶🏼、流浪成人👩🏽🍼、其他流浪儿童所控制🫄🏼、虐待🧎🏻♀️➡️;也有流浪儿童声称自己曾被保安与**(向荣,2002)。然而,国内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总体上🧟♀️,更多地聚焦在流浪儿童的犯罪现象上💇🏼♀️。有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包括流浪儿童在内的边缘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对于他们在街头的受害问题却少有系统的研究。人们习惯于将流浪儿童看作是危险的、仇视社会的🥯、可恶的“麻烦制造者”(陈晨,2004;席小华,2004)♖,而较少注意并研究他们受害的一面🦙。现存的一些关注流浪儿童在街头受害问题的研究🚶♂️➡️,又多属于对他们受害情况的描述(如向荣👷🏻,2002🦣🫸🏼;张齐安👶、杨海宇🏄🏻♂️,2002)👩🏿🎓,而缺少对群体受害过程发生的动态机理的分析。为什么流浪儿童特别频繁地遭受到外来迫害0️⃣♻️?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问题发生的动力机制怎样♟?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的主旨,是试图探讨𓀂、分析流浪儿童在流浪生活中的受害问题发生的动态过程。具体地说🟤,尊龙凯时娱乐将主要考察下列问题☠️:为什么流浪儿童更经常地成为适合的迫害目标?他们是如何成为加害者的猎物🙏🏼?在流浪生活中,流浪儿童能够获得哪些监护?流浪儿童是怎样应对外来迫害的?
二、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
本研究是笔者对有关上海流浪儿童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采纳YoungBarrett (2001)与Bemak (1996)等人的建议,尊龙凯时娱乐主要运用质性的民族志(Ethnography )的方法搜集数据资料。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给笔者提供了一个在“自然”情境中了解流浪儿童的机会,它使得笔者有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而与被笔者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从而深入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声音,获得许多其它研究方法所无法得到的翔实而可靠的数据。从2005年4月到2006年1月,笔者先后用7个月的时间在铁路上海站地区,观察😶🌫️、访问流浪儿🍆,先后在街头接触流浪儿童43人,用106天写就合计60万字的田野调查笔记。
依照Lincoln 与Guba(1985)的建议,我采用了多种办法去力图提高研究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首先,笔者调查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前后7个月🤷🏼♀️,做到了比较长时间的持续观察🦹🏽♂️。其次,笔者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包括实地观察、准结构访谈与无结构访谈的方法等🧗🏻♂️。在街头对流浪儿童的准结构访谈通常是在笔者自认为与流浪儿童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建立之后方才进行🧑🏿🎤。访谈的主题包括家庭背景🔆👢、街头生活状况、面临的暴力威胁等外来迫害以及应对受害问题的策略等。笔者对儿童的回答先是大概🐉、简要地予以记录,在结束田野调查后的当晚或者第二天再予以详细扩充🎅🏽。再次,笔者也将调查的一些重大发现(如下文要叙述的流浪儿童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等)与自己的老师、同事🥎、朋友予以探讨,试图通过同辈检验(Peer check)的方法来提高研究的信度;又透过成员检验(Member check)的方法,将对流浪儿童调查的发现与流浪儿童分享,邀请他们对本研究的发现是否合乎他们的情况予以评论🍇。
所有的数据资料都是在不断编码(Coding)🤐、反复比较(Constant comparing)的过程中按照主题进行分析的。本文引用的数据👨🏽🏭,在于说明流浪儿童在街头受害问题的发生的动态过程。
(二)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笔者在街头调查到的43名流浪儿童,其中又以两个流浪儿童小群体的11名流浪儿童为主。这些小孩的年龄在9岁到18岁之间👇🏼,文化程度都是在中学一年级及以下🦸🏻♂️。绝大部分是男孩,只有两名流浪女童。大部分儿童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以来自中西部不发达的地方(如安徽、四川、河南、山西等地)居多。流浪儿童在街头流浪的时间从1天到5年不等🥡。
(三)研究的地点
到2003年底🤹🏿♂️🕰,国内其它省市就有500万人到上海“打工”❤️,其中,60.8万为14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上海市统计局🤞,2004)🤿。尽管没有关于在上海的流浪儿童的统计数据,在过去几年🍫,大众媒体在不断惊呼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儿童到上海流浪🧗🏿♂️。
上海火车站是国内的一个特大型火车站,连同附近数个长途客运站迎送的南来北往的客人👏,上海火车站地区日客流量达30万人次(江跃中,2005)🏄♀️。上海站外围主要由南、北两个大型广场构成。其中👨🏽⚕️,南广场已经得到显著的更新。在其周围兴建起来的不夜城商城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北广场地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更新🚣🏻,市政建设落后,居民生活环境较差🐪,破旧的棚户区依然存在。其间的道路大多破旧狭窄,道路两旁的房子也多是低矮陈旧的老公房,吸毒👨🏽🦱、扒窃、卖淫嫖娼🥼、赌博等各色人等都混杂在此✊🏽,社会治安秩序相对不好(江跃中,2005)🆓。南北广场通过几条地下通道连为一体🧊。
选择铁路上海站地区作为调查的地点,是因为初步的考察发现,在火车站南北广场以及候车室内⛔💶,一直有不少流浪儿童流连🤷♂️;北广场那些破旧、廉价的小餐厅及其附近的永兴路的旧货市场,是不少流浪儿童常常光顾并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
三、调查结果
通过反复编码与比较,尊龙凯时娱乐发现,除了加害者的迫害🍂🪠、犯罪行为外,有三个主题(Themes)在尊龙凯时娱乐的资料中反复出现,并且与流浪儿童在街头的受害紧密关联:流浪儿童独特的生活方式;有足够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流浪儿童被动性的应对外来迫害的方式。
(一)街头生活及其作为受害标的(Target)的属性
研究发现🫕,在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儿童的受害问题的发生,与他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无论他们是主动离开家庭还是被迫离开,甚至根本就无家可归,在陌生的城市街头,他们都必须独立地面对生活,为自己的吃、穿、住、行与健康负责。这样独立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使得他们常常成为受害者,成为牺牲品。他们所能使用的谋生方式💱、可以选择的消费方式及其生活世界的基本游戏规则,无不将其迫入受害的境地🫅🏼,使其成为被侵犯的适合的标的🍽。
让尊龙凯时娱乐先以14岁的流浪女童花生米①的经历为例对此加以说明。2005年4月初的一个黄昏👉🏿,在和南广场紧邻的白玉兰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花生米很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同伴许亮——一个15岁的安徽籍流浪男童:“今天在广场上又遇到老沈阳⚖️👲🏿,当时差点没把我吓死!”许亮听闻后,显得同样的沮丧而忧伤👼,没有说什么话🔲。花生米依旧自言自语似地说准备去广州👩🦳,因为不敢在上海继续混:“不是混不下去,是不敢混下去……这里老板太多👆🏽,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是大哥。惹不起。”②根据她和许亮的叙说,老沈阳曾经很热情地请他们两个去住宾馆,他们毫无戒心地就去了。但是,去宾馆的当晚🙆🏽♂️,老沈阳就要他们去偷钱包👳🏼、偷手机👮🏼。两个人拒绝,结果当即就挨一顿“暴打”。后来,他们找机会从老沈阳手里逃脱出来🧍🏻♀️,并重新开始自己的街头生活。但是🥰,因为花生米与许亮一直在火车站附近流浪,所以经常遇到同样混迹在此的黑社会老大老沈阳🥤。每次看到老沈阳💃🏼,两个人就害怕,因为老沈阳扬言要杀了他们。花生米说不敢去广场了,准备离开火车站2️⃣。许亮一直不说话,只是在我佯装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多老大的时候”🪚🧁,他才有些愤怒、有些不屑地冲我脱口而道:“广场上偷东西的大哥多着呢!个子比你高👩🏼💼!身体比你壮!文身比你多!”
从许亮的忧伤、花生米的感慨,尊龙凯时娱乐可以清楚地看到流浪儿童受到黑社会成员胁迫的程度。他们被逼迫去偷窃🧚🏼♀️🦛,不从便遭暴力虐待,被威胁要处死。两个人甚至因此不敢踏入火车站南广场👩🔬。尽管如此📿,他们终于还是没有离开火车站。长期在上海流浪的经验🙇🏻♀️,让他们清楚地发现🏃♂️,与管理严格的人民广场、南京路、徐家汇相比,火车站是一个获取生活资源相对比较容易的地方🕊。作为未成年的儿童,法律严禁其进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无法如成人那样通过合法的工作谋生,而被迫进入到非正式的经济体系之中。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客流量特别大👨🏻🔬。因此,无论是捡垃圾🤧、卖报纸,还是从事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经济活动(Informaleconomic activities )或非法活动,赚钱谋生都比较容易。花生米说自己习惯了火车站,熟悉这里的警察、便衣🔠,也在这里寻找到了谋生的办法“钓鱼”——像钓鱼一样将投币电话机里的硬币钓起来🆑。因为上海火车站地区客流量特别大,所以投币电话机的使用率颇高🦐,他们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地赚到钱去继续他们的流浪生活🐼。而“其他地方钓鱼就赚不到什么钱”。因此,包括花生米与许亮在内的众多流浪儿都喜欢在火车站地区生活✫。可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在谋生方式上对火车站的依附,使得他们更多地暴露在黑社会成员的威胁中。如前文言及,作为一个陆上交通枢纽的上海站地区也一直都是违法犯罪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从逻辑上说⛈,只要花生米他们踏入南广场“钓鱼”🎟,或者捡垃圾、卖报纸🖇,总有可能遭遇老沈阳🍡、老新疆、大张等黑社会成员。这样的谋生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与黑社会成员共生的局面👳🏽♀️🛌🏽,也自然地增加了他们遭受黑社会暴力威胁、迫害的可能性。
如果说流浪儿童在赚钱谋生层面上对南广场的依赖增大了其与黑社会共处的概率,那么🍶,他们在日常消费方面对破旧的北广场的依附则进一步将他们推向有动机的侵犯者的生活世界。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地区,繁华兴隆的南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并没有流浪儿童赖以立身的空间。除去少有几个能够忍受他人歧视、白眼、驱赶的在南广场地区捡饭吃的小孩外👎,大部分流浪儿童的日常衣🧔🏻♀️㊗️、食、住都需要到棚户区、鱼龙混杂的北广场地区去解决。经济收入的限制👨🏿💻,决定了他们无法到那些相对较好并具有安全保障措施的社会空间生活,而只能在北广场棚户区或者南广场的露天广场度过他们的日日夜夜。然而😅,这些地方🥑🏊🏿♂️,却也正是有动机的侵犯者云集的地方。用流浪儿童小李的话说,“整个太阳山路上住的都是贼,各色各样的‘大哥’都住在那里🍿。”③这一现实,加大了流浪儿童被侵犯者迫害的机会。在6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注意到,16岁的流浪儿童安徽就5次在北广场地区被不同的黑社会成员暴力威胁,逼迫去偷窃手机、电动车、看守赌场等活动;15岁的流浪男童小贵也3次在该地区被“抓”去偷东西🤐;花生米更经历过6次这样的境遇。显然𓀂,这种因为经济上的局限而不得不委身于棚户之地的现实,也无形中将流浪儿童与一些具有动机的侵犯者放置在一起,使得他们成为那些侵犯者的猎物的可能性被提升✂️。
非但如此🤲🏼,因为流浪街头、独立生活,所以当流浪儿童之间发生争执🪹、冲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可以信赖的成人(如家长、教师、警察)给他们提供权威的规范与是非裁决。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流浪儿童慢慢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来解决争端🍾、冲突,寻得妥协与和平,从而形成一种他们生活世界的独特秩序👩🏽🏭。这个生活世界的游戏规则🫴🏽,以暴力为轴心✊🏼,他们倾向用身体暴力来解决争端🙅🏿♀️。这样一种独特的游戏规则,使得流浪儿童常常被其他流浪儿童殴打⚡️。例如,14岁的流浪儿张强就经常被花生米和许亮打。因为受到花生米的威胁,张强长期不敢进出花生米经常出没的南广场与白玉兰广场🧷,而只是在梅园路、联合售票大厅等火车站外围流连🧔🏽。他怕遭遇到花生米。他说花生米之所以要打他是因为他不肯帮花生米钓鱼☢️🂠,而花生米说自己打他是因为张强曾经欺负广场上一个更小的“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男孩⛓️💥,她要维护正义🙆🏽,“见不得他那老B 老样”。④当然,花生米自己也曾被一起生活的流浪儿童暴力虐待。例如,15岁的流浪男童斑点说😂,为了驯服花生米,安徽曾经把花生米反绑在一棵树上达一个多小时🥩🖋:
那是在晚上,安徽马上找来绳子🥯,尊龙凯时娱乐一起把花生米反绑在树上🌵,捆得紧紧的,把她搞哭了……那天晚上搞得她难过,安徽把她眼睛和嘴巴都用胶布黏起来🔊,留一个鼻子……至少一个小时……让她一个人在那里……要不是王哥⑤后来救了她,看她一个人在那里过一个晚上,哭啊🚍!
可见🕦,在遇到问题、矛盾、冲突的时候,流浪儿童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办法——使用暴力去解决。这背后潜藏的决定性要素👩👧👦,是他们缺乏负责任的成人的监护的社会现实🧹。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现实,他们才需要也才可能使用以暴力为主的手段去裁决。
(二)有能力保护者的缺席
在街头遭遇困难、面对外来迫害的时候,流浪儿童并不能如一般孩童那样能够从自己的父母👯👨🍼、亲属💉、老师、同学那里得到必要的信息、咨询与支持👩🏼🔧。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去应对包括暴力威胁在内的种种风险🚀、迫害。研究发现,在上海火车站地区🔱,当流浪儿童受害的时候,很少有具备足够能力的保护者在场有效保护他们𓀈🐨。无论是他们的朋辈、公众、还是国家的执法体系,都不能(或者不愿)有效地帮助他们去应对外来的迫害⌚️。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被害的可能性。
2005年5月14日🌧,也就是在安徽被大东北抓走后的第三天🤦♂️,花生米也被大东北抓到他们非法开设的赌场干活去了。这样👮,原来由东北、安徽、小贵、花生米、小虎与短毛等6个人构成的小团体,突然少了两个,而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个小团体的“头”东北因为盗窃被警察抓走仍未回来。所以👩🏼🔧🦐,花生米与安徽的被抓,让这个团体笼罩在一股悲怆凄凉的氛围之中🧖🏽♀️。当天下午🌯🧑🦼,在火车站南广场上,我遇见小贵,我问他花生米在哪里🧜♂️?他边走边沉重地说:“花生米死掉了,抓走了……大东北说了,再不去,大东北会把她杀掉👝!死定了!昨天晚上她自己过去的。”他说👷♂️,大东北让安徽回来让花生米去🎅🏽,花生米不敢不去。我跟随他一起到白玉兰广场上,遇见许亮。许亮很低声地对小贵说:“昨天花生米过来,让我去找东北🖖🏿,我到哪去找东北阿?……不可能找到。”对于找东北来解决问题的建议,小贵不以为然:“东北有个鸟用⑥👰🏽♂️,强哥都没有办法⚒,人家大东北有枪。”我问他找钱哥有不有用🧗🏿,小贵嗤之以鼻:“有个鸟用!你(指钱哥)打架厉害没用,人家有枪,你跑得再快,跑得过枪吗?”两个小孩窃窃相商,说话的声音始终很低,眼神落寞🔠,显得无可奈何👨👩👦。我继续试探性地问小贵报警有不有用📒0️⃣,不料,小贵更是嗤之以鼻:
有个鸟用🌳💽?!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人报警……报警👨🏿🍳?好啊🆗,最多(把加害人)抓起来🦸🏼♂️🤱🏻,拘留15天,出来后,你命都要没有。就算再厉害点,关他十几年🧑🏿🚒,他身边的人也要干死你👮🏿🎟。报警又不会判死刑🏄🏿♂️,判死刑还差不多……除非你不想再在火车站混,才可以去报警。
面对黑社会成员的迫害👨🦯,在流浪儿童看来,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空间。没有任何人或者社会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保护。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花生米一面顺从地去了大东北那里,一面想让许亮去找他们小群体的大哥东北来解救🖖🏽。然而,一来东北这个时候自己都已经被警方逮捕,二来根据小贵与许亮的说法,即使东北在也无济于事,就算是一度利用过他们、保护过他们的黑社会成员强哥和钱哥都没有用,因为大东北更强,“有枪”。这些孩童👂🏻,也不敢报警,因为他们的生活还要每天24小时地在火车站地区继续下去,而警察的保护最多只是一时一地。他们不敢从警察那里寻找保护🔰。那种公开的、消极的、事后算账性的法律保护,并不能够有效长久保护他们的身体安全。何况,按照花生米与另外一个流浪儿童陈晓驷的说法:“警察最赖!他们从来不管事🤞,就算见到尊龙凯时娱乐被别人打,他们也装着没有看见一样。根本就不管🧛♂️!”
那么👯♂️,在火车站地区,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为这些流浪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保护呢🗼?调查发现🚠,除了同伴与自己依靠的黑社会老大之外,在流浪儿童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还有两类重要人,一是其他在火车站地区流浪的大人,二是一些在该地区做生意的老板。不过,这两类人士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安全保护也非常有限。在张强被花生米等人暴力虐待的时候🦾,张强曾经诉诸他认的干哥福建——一个在火车站周边地区流浪🤾、拾荒的30几岁的福建籍健康男青年。但是,本分老实的福建有心无力,他在警告花生米不要欺负人家小小孩后,却遭受到了花生米带来的小李等一众流浪儿童的威胁:“你妈敢再罗嗦,连你和你弟弟一起打!打不死你🧎♀️➡️?!”面临这样的威胁,福建无可奈何,只是沉默地离开,留下张强独自遭受一顿猛打👭。实际上🐈🔯,就在张强挨打的时候,他认的干妈——张强常常光顾的一个餐厅的40岁左右的服务员——也就在旁边。但是,她能做的,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干儿子挨打,并没有及时施以援手。或者👸🏻,干儿子终究只是干儿子,并不值得她冒险保护🦽。
显然🌃,张强所认识的这些干哥、干妈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花生米对他的暴力虐待。类似地🚖🍯,当花生米被人以暴力威胁的时候👩🏿🦳,花生米认识的那些在外流浪的朋友与广场杂货店的老板娘🍇💂♂️,也都是无能为力。一个雨天的下午,花生米因为受不了老新疆的威胁,以酒解闷,终于喝醉👨🏽⚖️,睡倒在湿漉漉的广场上🕙。和她一起喝酒的30岁左右的残疾乞丐让两个和花生米熟悉的流浪拾荒者将花生米扶到白玉兰广场上去睡觉🛀🏽,两个人答允做了🥷。在白玉兰广场大约30分钟之后✍🏿,花生米慢慢清醒,挣扎起来,发现衣服全部湿透,便爬起来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要去北广场旧货市场买衣服🧇。两个长期和花生米一起混的拾荒的流浪汉贵州和光头主动跟上去,要陪她去。快要走到南广场正中央的小花园时,几个人突然遇到要抓花生米的老新疆和他的几个同伴。老新疆直接从两个人手中抓过花生米,光头起初不肯放手📠,老新疆顿时发怒,威胁要打人:“你给我放手🏭!”高个子悻悻然,没有说什么,自觉地放手。老新疆于是带酒醉的花生米朝地铁口走🤸🏿。贵州随即独自回往白玉兰广场,我和光头继续跟在老新疆等人之后。光头对我说,“花生米真的很可怜🧺,这么点大,人家都在家里享福🅾️。”我和光头走往老新疆停留的地铁口🌗,站在他们旁边👐🏽。老新疆敌视地看看我,看看高个子,起初没有说话。老新疆和他的同伴不停地恩威并用地要花生米跟他们去偷东西、“干活”,花生米就是不肯🦎。我和光头仍然站在他们旁边🦮。老新疆或者是不舒服🎒,抬头冲我说话:“你是她(花生米)什么人?”我说是朋友🙍🏻♀️💧。他迟疑地看看我,不说话👈🏽。半晌又充满挑战地问我👩🏿⚕️:“你是本地人👌🏿?”我说是。他慢悠悠地说,我看你就像是本地人🏡🧣,又冷冷地问我是哪个区的♣️,我很自然地说是“卢湾区的”。他便没有理睬我🐂,转过头向高个子厉声问道🧅:“那你是她什么人📮?”高个子说是“朋友”,老新疆从头到脚看了高个子一遍,厉声说“你他妈也朋友!什么朋友,看我怎么扇你!”高个子很是害怕🧖,再也不敢说话𓀍。不久后,我和光头离开老新疆他们🫄🏿,一起走回白玉兰广场。在白玉兰广场,一个19岁的刚来广场混的男孩告诉尊龙凯时娱乐🧎♂️,程石、刘峰、阿德等人听说花生米被老新疆抓住后🤵🤱🏿,都已经走掉了。难怪原来热闹的挤满流浪者的友谊服饰商场外的走廊💔,突然空荡荡起来🚣🏽♂️。可见🧜🏼♀️,在花生米遭遇来自黑社会的威胁的时候,与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流浪的大人、小孩都纷纷逃跑自保,他们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考虑如何帮助正在被老新疆控制的花生米,他们自己也害怕老新疆的威胁。而唯一有心帮助她🧙🏿📪、同情她的光头,在老新疆的威胁下,也终于选择了沉默🙎🏿、放弃、离开👨🏿💼。花生米就是在他所认识的一帮朋友的面前,被老新疆所威胁🩻、迫害📑🤳。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并不坚固可靠,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
可见,流浪儿童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国家的执法力量♦️🧑🏽🎓,都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不能够有效阻挡来自有动机的侵犯者的威胁、迫害。在火车站地区🐯,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有能力的保护者能够有效确保流浪儿童的安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有限🤦🏻♀️,使得上海站地区的流浪儿童经常性地处于一种有能力的保护者缺位的状态之中🚫,由此进一步导致针对流浪儿童犯罪的侵犯者、适合的标的与有能力的保护者缺位三个要素的高度统一🙅♂️,是为街头流浪儿童受害的重要机理🫠。
(三)被动性适应(Passive adaptation)
儿童并不只是一个脆弱的“未成年人”🙏🏼,他/她不仅有脆弱的一面,也有其能动性与克服困难与危机的弹性(James ,Jenks,Prout,1998;James Prout,1997)🙋🏽♀️。不过📲,本研究发现,在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迫害的时候🏬,流浪儿童的能动性仍是比较有限。由于他们生活世界的机会结构的限制,他们并无法找到应对这些暴力威胁🌡、加害的有效办法,进而促进自身的正面🪓、积极发展。相反,在外来侵犯面前✫,他们大多只能被动🐒、消极适应。
调查发现,上海站地区流浪儿童应对外来迫害的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寻找黑社会的帮助。黑社会成员,对于这些小孩来说🔴,具有双刃性。一方面🤏,流浪儿童畏惧被他们抓、打、逼👉🏽✋🏽;另一方面,一旦跟了特定的老大,也就有人“罩”,⑦老大一般都会承诺为他们提供保护🧔🏽♂️。只是🥡,承诺归承诺,行动归行动🤾♀️,地下社会有地下社会的游戏规则。老大在考虑出手帮助被人迫害的流浪儿童的时候,也会理性地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这就是小贵在讨论如何营救被大东北抓的花生米的时候说到的,找东北、找强哥、找钱哥都没有用的原因所在🧑🏿🎨🛃。此外🤹🏿,小孩自身也并非总是愿意从黑社会老大那里寻找帮助📌。每一次受助的过程,都意味着小孩对施助者的依赖的加深,意味着施助者对小孩控制的加强。这对于习惯了自由的流浪儿童而言,同样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老新疆不断地威胁花生米去偷窃的时候,花生米依然不想找强哥来帮忙,原因在于“要是找强哥的话,就意味着要顺从强哥,那两天就要交一个手机,还是不好混”。二是逃跑,尽可能远离暴力源。当花生米不停地要揍张强的时候,张强采取的策略是不再到花生米常常光顾的南广场📚、白玉兰广场上去玩🚭,而只是在梅园路、火车站联合售票大厅等火车站地区的外围活动;当老新疆不停地威胁花生米的时候🏖,花生米的应对是“打不起,还躲不起吗”的逻辑🍭,她曾一度独自逃跑到南京路步行街去混👩🏿🚀;当许亮受到小李的暴力虐待与威胁的时候😑,他干脆远离上海,跟一个流浪汉爬火车去了遥远的四川流浪。三是寻找朋友、同辈的帮助🤦🏻。如果威胁他们的是一般的流浪儿或者在外流浪的大人🏌️♂️,而不是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他们通常都能够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然而🦈,当他们面临黑社会的暴力威胁的时候,如上文讨论的🧞,这个策略通常都没有效果。四是屈从。尽管流浪儿童不愿意忍受被人控制🫲🏻、为他人干活并承担风险💾,有时候,面对黑社会的胁迫🤤,这些小孩选择了屈从。他们无法抗衡黑社会的这种威胁,如同安徽解释的:“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不去,就要打你!”
总体上🤏,流浪儿童自身应对外部威胁的策略概属消极🎖✭、被动。而这种被动应对🤛🏻,让有动机的侵犯者(如黑社会成员)更加毫无顾虑🛃,进而增强了流浪儿童作为“适合的标的”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流浪儿童面临外来加害时候的消极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针对他们的迫害行为。
四、结论与讨论
流浪儿童是一个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他们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也表现在他们的人身安全保障的缺乏(De Venanzi,2003)。在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城市街头😛🏇🏻,上海火车站地区的流浪儿童常常要遭受他人的迫害;而蕴含着流浪儿童遭受暴力威胁与迫害的可能性的,正是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贫乏。
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充分支持、印证了Cohen 等人提出的日常活动理论。在Cohen 等看来,犯罪行为的发生通常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动机的侵犯者(Motivated offender)、适合的标的(Suitable target )和有能力的保护者不在场(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ship )——在特定时空中的统一📣、汇合(Cohen ,Felson ,1979)。正是有动机的侵犯者🙍🏻♀️、适合的标的与有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等三要素同时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出现🗣,导致了针对流浪儿童的迫害行为频繁发生。流浪儿童的独特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与有动机的侵犯者常常遭遇、共处的现实,进而增强了他们作为“适合的标的”的属性,增加了他们被害的风险。在城市街头,流浪儿童被排斥在正式的经济体系之外🖖🏼⛅️。然而🧘🏻♂️,当前,并没有专门面向流浪儿童的社会性服务存在于上海的街头👐🏼🤥。在上海🧝🏽,政府应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制度性的办法就是设立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但是,这个中心坐落在比较偏远的位置,而且没有开展外展(Outreaching )服务,大多数流浪儿童都不知道如何前往接受救助。因此,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无论是寒冷、饥饿还是孤独,流浪儿童都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去应对。这就迫使流浪儿童进入到非正式的地下经济体系之中,迫使他们的日常生活边缘化,由此使得他们滑入到充满风险的地下社会之中。如本研究发现的🤾🏽♂️,在上海站周边的流浪儿童的衣💬、食、住大多是在破落危险的北广场进行👩🏻🦽➡️,而那里正是有动机的侵犯者云集的地方🙎🏽♀️。这是流浪儿童遭受外来迫害的风险相对较大的第一个制度性要素。
Cohen 等所谓的有能力的保护者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缺席,是导致流浪儿童受害的另一个制度性因素🥧。在离开了父母、家庭之后🩸,国家本来应该扮演起自己作为儿童成长的终极监护人(Ultimate guardianship )的角色,保护好流浪儿童。但是🧂,本研究发现,在上海火车站地区🌔,国家执法部门却没有长期有效地去保护流浪儿童,甚至根本不采取积极对策去保护这些无人监护的流浪儿童。另一方面,流浪儿童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使有热心的朋友,却因为诸种原因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流浪儿免受暴力威胁。这就为针对流浪儿童的加害行为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在客观上增加了流浪儿童受害的可能性。
造成Cohen 所谓的犯罪三要素在流浪儿童生活世界的高度重合,确实与流浪儿童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流浪儿童自身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街头的暴力威胁🧄。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使得流浪儿童常常受害的原因在于流浪儿童自身能动性的欠缺🛍🉐。当我置身在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一起面临黑社会成员的威胁的时候,我常常非常深切地感受到结构性制约的不可抗拒性。换作是一个成年的我,倘若不得不每天24小时地流浪街头又得不到政府执法部门的有效保护,面临黑社会的威胁的时候👩🏼🦱,除了像那些年幼的流浪儿童那样选择逃跑或者消极承受的办法👨🏻⚖️⭐️,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道路可走呢?
另一方面,尊龙凯时娱乐也不能将流浪儿童的受害问题的发生简单归结为有动机的侵犯者增加的缘故👰🏻♀️。上海火车站地区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但是👨🏼🏭,流浪儿童遭受的外来迫害却特别频繁。要理解这个问题👢,尊龙凯时娱乐也许应该从国家作用的发挥这个层面开始进行探讨。无论是造就流浪儿童作为“适合的标的”的属性的生活方式🧑🧒🧒,还是街头有能力的保护者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因为“国家缺席”(Absence of the State)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流浪儿童在街头得不到及时必要的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他们才不得不在生产性与消费性实践的过程中都依附于那些缺少良好安保措施的场域;正是因为国家未能充分扮演起这些失去自然监护人的孩童的终极监护人的角色的原因⚀,才使得流浪儿童在街头遭遇有动机的侵犯者的时候♾🧟♀️,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注释🎊:
①为了保护流浪儿童的隐私,本文涉及的人名——无论是流浪儿童、黑社会成员或流浪成人的姓名——都是笔者编造的匿名。
②“老板”💗、“大哥”都是流浪儿童对黑社会老大的称呼。
③太阳山路是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一条道路名,位居北广场棚户区的核心地段。
④“老B 老样”是上海站地区流浪儿童常用来骂人的贬义词汇𓀃,其含义大概为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傲慢、目中无人。
⑤王哥是这些流浪儿童常常光顾的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当时,安徽与斑点将花生米绑起来的地方就在这家饭店前面的马路旁🐏。
⑥“有个鸟用”系本研究接触到的流浪儿童的日常粗俗用语之一♟,大意为“根本就没有用”。
⑦“罩”是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儿童常用的另一个术语🙎🏻♀️,专指他人(尤其是地下社会人士)提供的法律之外的保护伞、保护✍🏽。
参考文献⏰:
[1]陈晨:《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重中之重——心理矫治》🧑🏽🎄,载《社会福利》2004年第5期👩🏽🏫。
[2]江跃中:《让“上海脸面”两边都靓丽——闸北区用大手笔为铁路上海站北广场“整容”》,载《新民晚报》2005年1月22日。
[3]马美菱:《跪拜求施升级为拦路索讨,少年肢残原本是造型伪装,街头乞讨不管不行》,载《文汇报》2003年11月15日。
[4]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5]吴立德🧏🏼♂️:《上海街头乞讨人员增多🍬,救助管理亟需形成合力》,载《城市导报》2003年12月13日。
[6]席小华:《犯罪流浪儿童的司法保护》🧓🏽,载《当代青年研究》2004年第6期。
[7]向荣:《流浪儿童研究》😟,载张和清等主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国财政出版社,2002年。
[8]严海波等:《关注中国城市流浪儿童——徐州市流浪儿童状况调查》🧚🏽♀️🈸,载《青年研究》2005年第2期。
[9]张齐安、杨海宇:《中国流浪儿童状况和救助对策》,载《社会福利》2002年第9期。
[10]Anderson ,S.,Hou🕴🏼,W.(2000)。Children in need of specialprotection:end of cycle report.Retrieved October7👩🏽🎨,2004,from http://www.unicef.org/evaldatabase/CHN—2000—009—part—1.pdf
[11]Aptekar👩🦯,L.,Abebe,B.(1997)。Conflict in the neighborhood:Street and working children in the public place.Childhood ,4(4)👨🌾,477—490.
[12]Bemak,F.(1996)。A new paradigm redefining future researchwith street children.Childhood 🪵,3👂🏽,147—156.
[13]Cohen👷♀️💆🏻♀️,L.E.,Felson ,M.(1979)。Social change and crimetrends👋🏽🧑🏼💼: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4,588—608.
[14]De Venanzi ,A.(2003)。Street children and the excludedcla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4(5)🤾🏼♀️,472—494.
[15]Kidd ,S.A.(2003)😭。Street youth 🎤:Coping and interventions.Child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20(4),235—261.
[16]James,A.🤦🏽♀️,Jenks🐜,C.,Prout👩🏿🦰,A.(1998)🦜。Theorizingchildhood.Cambridge:Polity Press.
[17]James,A.,Prout,A.(1997)🗒。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2nd ed.)。London 😪:Falmer Press.
[18]Lincoln,Y.S.,Guba ,E.G.(1985)。Naturalistic inquiry.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Young🧋,L.🧆,Barrett,H.(2001)。Adapting visual methods:Action research with Kampala street children.Area ,33(2)🏓,141—152.
作者简介🛍️:程福财,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邮编200020)
原文出处:《青年研究》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