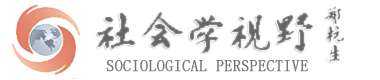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劳教制度的存废与出路
王鸿谅
文章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2012.9.13
摘要🚪:先后被列入两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一度被视为取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最终方案,令人困惑的是,草案虽然早已完成,也征求过中央各部委💁🏻♂️、专家学者多轮意见👂🏻,却再无下文,迟迟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劳教的异化
劳动教养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肃反时期✊。关于劳教的最早法律,是1957年8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按照《决定》的说法🤩,设置劳教制度,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将劳教作为肃反工具或维护政治稳定举措的设想🏩,在经过一年试行之后🔑,让位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国务院不仅将劳教定位于一种强制教育改造措施,还把它视为一种变相的就业安置办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决定》甚至没有明确劳教的期限🍨,只笼统规定需要实行劳教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实践中,实际是由公安部门一家管理👮🏼。
但是劳教的执行,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决定》出台后,全国从市、县、乡、公社甚至到生产队👨🏻🚴🏻♀️,纷纷兴建劳教所🏄🏼,关押各类“不听话”和“不老实”的人,如巫婆👩🏼⚖️、神棍💁🏼♂️、懒汉、二流子等😑,上海甚至连拒付子女生活费和抚养费者都送去劳改🏄🏽🟡。按照“司法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到1957年,全国只有36983人被劳动教养🖐🏼。从1958年开始🦹♀️🫶🏽,全国收容劳动教养人员的数量急剧增长,当年末收容人数达到355777人,1959年达到435325人🚔,1960年达到历史最高峰,499523人🫚。
公安部也意识到劳改有“扩大化”倾向。1961年👱,一些地方出现了被劳教人员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当年4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期限一般为2年到3年,扭转了“劳改有期👨🎓,劳教无期”的思想🤵🏽♂️。全国随后对劳动教养场所进行了大规模清理整顿。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进入法制重建时期👰🏿,劳教制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首次明确劳教期限为“一年至三年”🎇,但“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方法》(简称《试行方法》)。《试行方法》将劳动教养定义为:“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补充规定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按照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的解读🔺,这就意味着劳动教养的审批权虽然表面上属于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等行政机关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但事实上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公安机关统一行使。
从1957年的《决定》到1982年的《试行办法》,劳动教养在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上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从强制实施劳动教育和安置就业,逐渐成为中国行政处罚措施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带有明显的处罚性🐻。之后十几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将更多人员纳入劳教范围。尽管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第8条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但还是有不少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出现了劳教内容,劳教对象也进一步扩大。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所言,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劳动教养是剥夺公民的自由时间最长🦒、适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行政处罚措施”。
对于地方性法规肆意扩大劳教对象的做法👩🏿🌾,司法机关曾考虑进行规范。但是👦🏼🧷,这种系统内的规范,仍然无法遏制劳教扩大化的趋势🏛𓀌,劳教成了一个为大局服务的“治安箩筐”,从打架斗殴、吃喝嫖赌到缠诉上访、诽谤官员,无所不包。
变革的困局
劳教制度早就是众矢之的。每年“两会”✧♿,都有废除劳教的呼声,2004年联名要求废除劳教的人大代表已经多达400多人。法学界也纷纷撰文批评劳教制度👩🏼🦳,北京大学的陈瑞华教授就认为:“在我国的行政处罚程序越来越走向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时候,劳动教养程序却仍然保持了书面的🦟、间接的♦︎、单方面的、不透明的审查和救济方式。这显然与整个国家行政程序法制化的进程背道而驰🚨。”清华大学的张建伟教授则批评说🚊:“在劳动教养案件的处理中,公安机关不仅充当了调查者🚣🏻♂️、控诉者的角色,还扮演了裁判者角色,这种追诉性质的职能与审判行政的职能集于一身的现象⚒🤦🏿♀️,是典型的行政🤹🏼、司法不分。”
改变势在必行。200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司法改革进行战略部署,文件决定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造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这项改革工作。《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起草工作随之启动,并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的立法计划🐣🤌🏻。
但是,由于学术界、立法部门和实务部门在教育矫治的决定程序上都存在重大分歧,《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始终没能进入立法审议程序🙅🏼♀️。一位参与讨论的学者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决定权的归属上”。“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对劳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造,由基层法院通过简易司法程序,做出教育矫治决定。这种意见符合国际公约要求,得到了全国人大法律委🫧💾、法工委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后🫸🏽,应由公安机关做出教育矫治决定🐦🔥,同时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赞成这一意见的主要是全国人大内司委💂🏻♀️、公安部👩🏻。”
分歧的背后🚴🏿,还是权力的配置与均衡。中央政法委、立法机关多次开会协调,最终决定暂缓审议相关立法,继续由公安机关保留劳教决定权。这么考虑的理由是:第一,当时相当一部分利用邪教进行的违法活动不适合走司法审判程序👟;其次,依照相关法律,公安机关本来就有权决定采取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医疗、强制治疗等17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第三,由法院行使教育矫治决定权,需要增设法庭、增加法官🌹,人力🖐🏿、财力成本太大。
2008年,中央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配套下发的文件再次决定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并明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国家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所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这次改革的思路,是对原来的劳教对象进行适当分流🕍,将吸毒人员纳入禁毒法规定的强制戒毒和康复戒毒范围(2008年7月1日实施的《禁毒法》规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做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最长可以延长1年。这样就将原本通过劳教处理的对象分离了近50%),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社会治安和稳定的行为,以及多次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通过修改《刑法》,纳入刑罚处理范围😔,对上述人员之外的部分违法人员,集中实行教育矫治。
2009年5月,法工委形成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草案暂时绕开了上次的司法化之争,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委员会👏🏿,行使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措施的决定权。基本框架是:设区的市以上各级政府设立教育矫治委员会𓀑,成员由本级政府、公安、司法行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有关负责人担任☄️🎖。教育矫治委员会根据公安机关的提议,负责审议决定是否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教育矫治。检察院对教育矫治决定、执行和解除实施法律监督🧜🏼♂️。
在当前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形势下🤹♀️,到底要不要舍弃公安审批模式,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个草案征求过中央各部委、专家学者多轮意见之后🐻❄️,迟迟没有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𓀃,折中的结果是暂缓立法🤛🏽,先行试点🤷🏻♀️。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个部委联合发布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将兰州、济南、南京、郑州四地作为试点城市。试点方案下发后,四个城市都成立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政府法制办、教育局、民政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妇联等机构的负责人。试点正在进行中⚧,耐人寻味的是,教育矫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依旧不约而同地设在了当地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