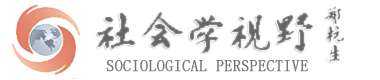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本报记者张健
李泽厚如是说——
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
记者:《论语》非得要“摘录加心得”才能“慰安人际”吗?干嘛不直接读《论语》?能讲一下国外宗教思想的传播方式吗?
李泽厚💻:《圣经》并不是孤零零的一本书,它有很多解释它的书💁🏽♂️,还有一些电台专门解释教义,有专门设计给儿童看的,配了很多彩色图画,编成故事,销量很大🧑🏼🎄。此外,教会还会免费赠送一些书籍。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下,当然需要针对今天人们的问题和状况来“摘录加心得”,作出解释发挥♨️。
记者:在美国,有没有播音员因为讲《圣经》🤳🏿,像于丹一样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
李泽厚:美国人做这个事情很久了🖐🏿🪸,人们习以为常🫁。尊龙凯时娱乐突然地出了一个于丹🎇,所以一下子很火⛴🙆🏼♀️。美国很多人一星期去一次教堂,宗教行为已经不知不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没有这种现象。
记者🫙🐨:孔子不忍“礼崩乐坏”而追求“克己复礼”,于丹迅速深得人心,是否说明当下近于“礼崩乐坏”?
李泽厚: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我刚才说了,虽然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关系淡漠🫥,每天都在计算金钱👨❤️💋👨,这些都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所以讲一些孔夫子的东西🏋🏽♀️,能够安慰他们🏌🏻♂️,启发⏺、引导他们。
记者:可美国人物质生活也很丰富啊。
李泽厚🕺🏽:它的宗教传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如果美国没有宗教,那问题就会更大了。
记者:1919年后🫅🏼,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是否此前,礼乐有序?
李泽厚:此前有礼教,“文革”前有毛泽东思想,人们讲诚信。为什么,他们有信仰,毛时代信仰共产主义。对于个体来说,有一个信仰,生活就会充实很多🔧🌲。现在是信仰丧失的时代,道德丧失的时代。所以大家就感觉“礼崩乐坏”了🍋🟩🎰,无论对事还是对人,人们没有了准则,有人不知所措🚙,也有人无所不为。于丹讲这个🦹🏻♂️,不就是为了大家生活快乐、心灵快乐嘛👸🏿。这个就是起到了宗教性的作用。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有半哲学半宗教的儒学和礼教,如我反复讲过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某些宁要信仰不要命的生存方式?
李泽厚:这就是信仰麻烦的地方,信仰有时候是上帝,有时候是魔鬼。美国有过人民圣殿教🤨,将教徒集中在一块🧕,然后杀死,这是邪教。美国还有其他类似的宗教,它们也有信仰🏌🏻♂️,却信仰了魔鬼🕡。但是,全世界那些大的宗教🟧,能够绵延那么广,持续那么久,有那么众多的信徒,就有它的理由🤽🏼♀️,它们一般是有益于社会和大众的。
记者✶:您觉得于丹的错误都能容忍吗?
李泽厚:错误是免不了的嘛⚛️,何况《论语》很多地方就有多种解释,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她大概是解释错了🎩,但是改了就行了嘛,没有必要抓住这些大肆攻击。当然,人各有分工,但是基本的意思还是不能错的。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于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重新产生对中国经典的兴趣。20多年前,反传统最厉害🧑🏼🏭,现在🎐,又突然觉得传统好得不得了,都不对,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每个传统都有坏的东西。
记者🍤🎹:回到一个旧有的争论💇🏿♀️🐵,它的关键词是📱:精英、平民和思想史。
李泽厚:你讲的可能是指当
记者:那您将于丹放在什么位置🥹,平民还是精英?
李泽厚: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她自己也承认是布道嘛,布孔子之道有什么不好呢?人们觉得需要她,觉得她讲得好🖐🏿,能打动人心,这就很不简单,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要那么多学者干嘛,什么人都要做专家学者干嘛。
记者:学者不需要很多,那么布道士呢🙍🏻🧑🏽⚖️?
李泽厚🕣: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去年我就说💪🏽,余秋雨、易中天、阎崇年很不错,我支持他们上电视讲坛🔎,他们讲历史,按照正史来讲。现在老百姓了解历史是通过电视剧,好些电视剧乌七八糟胡编乱造。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有什么坏处?当时😐👨👩👧👦,易中天不是也被人攻击得很厉害吗👨🎓?
记者:易中天比之于丹,谁更能称作为布道士?
李泽厚:易中天讲的是历史故事♎️,而于丹讲的是为人之道,那当然更受关注。前者不是“布道”,后者却涉及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单纯是知识🎁、趣味,当然更为老百姓所需要。儒学是有宗教性的💹,港台的新儒家🪰,例如牟宗三🎍,便把儒学的宗教性挖掘得很深,但那是在书斋里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说你那个大讲宗教性的儒学却算不了有宗教性🧍🏻♂️,因为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没几个人懂☝🏼🛂,根本到不了老百姓那里去。只有学术意义,没有社会意义,起不了宗教或宗教性应起的作用🎫🤷🏻♀️。
记者🫃🏻:那您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布道者🏩🔒?
李泽厚: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尽管他的《人间词话》销量也不小,但那是累积的长期的🙆🏻。以前有人问我对学者从政从商怎么看,我说那很好啊,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挤着做学者呢?每个人的才能💪🏿、性情♏️、境遇都不一样,人应该按自己的主客观条件来做自己能做和愿做的事情🤘。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来维持生存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挤在一条通道上🫅🏼,即使这条通道如何宽广美丽,也不必要。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𓀎,1990年代起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